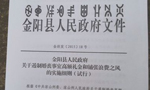2016-01-25 0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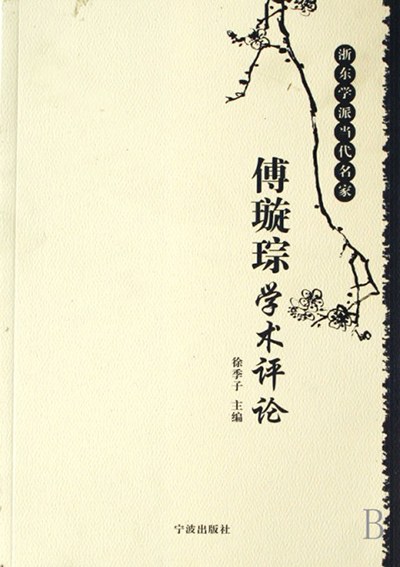
据说,这是宁波数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夜。就在寒风呼啸中,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则直打寒战的消息:当代著名学者、出版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仙逝了。顿时感到一阵惊愕。
悲痛叹惜之余,我从书架中取出了这本《傅璇琮学术评论》。打开扉页,傅先生的亲笔题签墨香犹在:
“此书编纂、出版,多承吴学军同志精心校订,谨此志谢。/傅璇琮/二〇〇七、七、卅日/宁波”
我用僵了的手指翻开书的一页一页,思绪也随之回到了二〇〇七年。因为这本书,我曾和傅先生有过数面之缘,有幸见识过先生的大家品格、长者风范,想来至今如沐春风。
那时,我还在宁波出版社当图书编辑。可能因为我经手编辑的《智者之香》《中国的吉普赛人》《宁波的中国之最》等书还略微像样,因此那年春节刚过,便接到马玉娟社长交付的一个重要任务:给徐季子先生主编的这本《傅璇琮学术评论》当责任编辑。
接过厚厚一叠书稿后,我心中不免很是忐忑。毕竟我还只做了一年的图书编辑,而这本书却是罗宗强、陈允吉、程千帆等三十余位学界名家对傅先生学术研究的综述评论,其内容主要涉及唐宋文学研究,引文众多,文字深奥,用典偏僻,不易编校。尤其是傅先生本人即是当代著名出版家和编辑大家,以我这样的出版新兵为傅先生这样的前辈名贤当责任编辑,实在惴惴不安。不过,不安归不安,活终究是要一点一点干出来的。因此,我花了不少工夫编稿子,对于许多一时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都一条一条作了笔记。
转眼到了三四月间,有天马社长告诉我傅先生来宁波了,有问题可以当面请教。这可是我期待已久的。那时,出版社还在苍水街,傅先生就近住在对面的联谊宾馆。第二天,我就自告奋勇开车接他去新芝宾馆开会。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他个子不高,精神很好,敦厚温雅,平易近人,对待我这样的后生晚辈也非常客气。坐的是我的第一辆车,档次不高,还比较小,但老先生一点也不在意,连说好几次“麻烦了”、“辛苦了”。那天正好是雾霾天,漫天灰蒙蒙的,看不了多远,连车子上都铺了淡淡黄沙般的一层颗粒物。傅先生感叹道:“这天气,北京这样,没想到来宁波了还是这样。”
初次见面还有点生疏,可能傅先生也确实“内向不喜言谈”,因此我除了请教编辑过程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基本没有谈及其他。我把前阵子列的编辑疑难杂症单子拿了出来。傅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先带回去,好好想一想,再答复你。”
过了两天,我们又见面了。傅先生拿出那张单子,耐心地一条一条解释说明,还谢谢我细心找出了几处前后不一致的文字。有些问题,他还以商量的口气让我看着办,说并不一定以他说的为准。现在想来,有几个问题简直是低劣之极,但他也同样一一认真作答。我很不好意思,可能脸都快红了吧。傅先生安慰我说:“我们(中华书局)那边也一样,老编辑总是从年轻编辑开始干起来的。”让我略解尴尬。
这本学术评论集,不仅收录了学术界专家教授对傅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德行情操的评述和专论,书前还要放上傅先生学术活动以及他和名家往来书信的照片。他拿出一个用旧了的大信封,从里头拿出钱锺书、启功、饶宗颐、黄苗子等十多位名家寄他的书信,一些照片,以及他捐赠给天一阁的十多种著作书影。他将每张原件都编了号,对应着写了文字说明,对钱锺书先生的手札还专门以简体字释写了一遍,点点滴滴中显示出一个大学者、大编辑家、大出版家的严谨笃实。傅先生嘱我要仔细处理这些原件,扫瞄电分后要保管好,下次要归还他。我知道,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学术史料,我这个后辈小子能经手,也是一种福分了。
书中要放一张傅先生工作照,但他手头有的大多是极普通的日常照片,我觉得不太满意。便请来宁波晚报的赵磊(网名石头)掌镜,约好当天下午专门为傅先生拍一张照。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宁波军分区边上的枫林晚书店,也没和老板郑永宏打招呼,只管自己慢慢找书、翻书。借着午后温暖的阳光,赵磊拍摄了十多分钟,经傅先生认可,最终选用了现在这张作者像。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似乎有些熟了。我因为当过宁波日报的文化记者,本性难移,所以开始问一些本书之外的问题。记得我有些“放肆”地问傅先生,他名字中的“琮”字,字典上念CONG,但实际上许多人都念ZONG,那到底应该怎么念?先生答道:“没关系,名字就是让人念的,从俗好了。人家习惯念ZONG就这么念,我也答应的。”另外,他也谈及自己个人的研究专著,如《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诗论学丛稿》《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基本上都不在中华书局出版,以免人家误会。傅先生以中华书局总编辑之尊,而甘愿放弃在自己主管的国家顶级出版社出书,这在物欲横流、普遍寻租的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傅先生此番回京之后,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主要是请他审定书的版式和封面设计稿,他对于封底的钱锺书先生题签、封面的梅花饰条、书眉的飞天底纹等设计都表示满意。在编校过程中,傅先生又寄来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教授于当年四月七日补写的《新记》。当时全书已经大体排完,但我用其他字体将此补写的部分放在这一篇的开头,以体现学界对于傅先生为新时期浙东学派代表人物的高度认同。
到了六月,这本400多页的《傅璇琮学术评论》终于通过编校、审读,可以清样了。傅先生对于样书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他说,能够这么顺利出版已经很好了。我也有如释重负的喜悦,心情一激动,便说有个想法,想写一篇关于傅先生出版编辑思想的论文。傅先生听了,很认真地让我可以先参考一下相关资料。
七月底,傅先生再次回甬,拿到了刚刚出炉的新书。他拿着书,说应该送我一本,但要回房间写好字再给我。吃过饭后,傅先生让我过去,把题签并签名过的这本书给我。同时还有一本签名本,让我转交给为他摄影的赵磊。另外,他还送我一本专业杂志,里边有一篇关于他的专访。原来,上回傅先生提到过的论文参考资料,竟然专门带过来给我了。这让我真是万分感动。
八月廿八日,宁波市委宣传部专门在新芝宾馆为本书举办了隆重的首发式。还是我开车接送的。路上,傅先生说起《宁波通史》马上要定稿付梓了,我编过这几部书,对宁波的历史文化大致有些了解,应该也要参与编辑。但是,我女儿刚刚在七月份出生,几乎和这本书同步面世。由于薪水不足以养家糊口,且无法解决编制等原因,我基本上决定要离开出版社了。傅先生的这本书,竟然是我短暂的出版编辑生涯中的最后一本。这点想来至今唏嘘不已。
我记得傅先生还是话不多,但明显不表赞同,并且颇不理解。他说:“我始终觉得当编辑是一件乐事,尤其是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专业编辑。现在出版界越来越注重市场和利润,但如果只追求经济效益,那些很有价值但不一定有市场的书就没人出了。一个人,不应该太受外部的诱惑或冲击,即使长期在出版社工作,不在大学或研究所,也能学有所成的。”
惭愧得很,不久后我还是离开了出版社。此后,我便落入杂碎公务的窠臼,不学无术,和出版界基本没有工作联系。傅先生的名片还在,但此后和他再也无缘交集。尤其羞愧的是,关于傅先生出版编辑思想的论文,我也曾收集了些资料,作了点笔记,但因为人已不在出版界,故而一直没有动笔。而现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冷的寒冬之夜,“一心为学,静观自得”、“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的傅璇琮先生溘然离去了,也许这正是他“避易就难,避热就冷”的治学道路的终点。
一想至此,夜已深了,人愈发冷了。此时,四明山正大雪盖地,白茫茫一片最是纯粹。书和学术的天堂,想必也是如此。
傅先生,此去山高水长,一路走好!
作者 吴 空
编辑: 孙研
- 浙江调查:五成女职工担心生二孩影响饭碗
- 杭州体彩中心官员借考察组织公款旅游
- 列车员报错站 百余乘客寒冬凌晨下错车
- 女子为露锁骨不穿秋衣 散步十分钟冻瘫
- 新郎雪夜“逃婚” 新娘:等你回来娶我
- 美国罕见强暴风雪致25人死亡 纽约发出禁行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