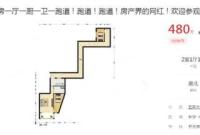《测绘学概论》课后学生排队找院士签名。
每年秋天,当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梧桐叶开始飘落,6位院士会从天南地北的会议中抽离,陆续回到一方不大的讲台上。
台下是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这些大一新生刚从应试教育中浮上来,他们邂逅的第一位老师,就是院士。
这是一门叫作《测绘学概论》的课程,由6位院士、4位教授共同讲授,有人称它为“最奢侈的基础课”。课上不点名、不签到,阶梯教室后排却挤挤挨挨站着人。课后,找院士签名的学生排成长队。
20年间,这门课走进了武大的通识课堂,走进了千里外的同济大学,听过课的学生上万人次。最初,院士们仍需亲自拿着笔尺,将课件画在薄薄的透明胶片上。如今,带有动图的多媒体课件取代了胶片。时间也改变了几位科学家,他们变成平均年龄77岁的老人,师生年龄相隔半个多世纪。
不变的是,站在讲台上,几位院士仍会常常提起自己的“老师”——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下文简称“武测”,2000年与武汉大学合校)的创始人、新中国测绘界的大师们。坚持给本科新生上课的传统,始于这些“老师的老师”。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甚至用生命守护一方神圣的讲台。这一代院士,从老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只不过,他们需要对抗的东西,早已不同了。

在德国留学时,陈永龄、夏坚白、王之卓与友人合影。
理想的大学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
开始讲课前,李德仁院士习惯走向讲台中央。年近80岁的他缓缓弯下腰,鞠上一躬,仿佛音乐会开场了。
200多人的大教室里格外安静。有人托着腮,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眼前的老人。站在台上的老师,正是他们桌上课本的编者之一。
宁津生、陈俊勇、张祖勋、刘经南、李德仁及龚健雅,这6位院士被认为是测绘学领域内的“传奇”“一代奠基人”。但在这门课上,他们是最普通的授课老师。
“理想的大学应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这里碰见一位牛顿,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有人用林语堂的名言形容这门课。
武大学生则霸气地称这些院士为“测概天团”。“集齐签名,召唤神龙”。
这个“偶像天团”,看上去和时髦毫不搭边。他们是一群“爷爷级”的老头,年纪最大的85岁,最年轻的一位60岁。在难得的合影中,6位老人有些拘谨地站成一排,双手大多叠在身前。镜头清晰暴露出他们额前稀疏的头发、岁月在脸上留下的一道道褶子。
宁津生院士是这门课的发起者。今年85岁的他,对流行文化的印象,还停留在10多年前。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地测量学家,笑呵呵地说,学生找他要签名时,他有种成了“超女”的恍惚感。
这门课讲授的内容,没有那么“高深莫测”。从课程设计之初,院士们就统一意见,要尽可能地贴近年轻人,“不能吓跑他们”。讲义中拗口的概念删了又删,教材特意制作成彩色,插画、图示几乎占了一小半。
整整20个课时,6个院士,4个教授,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测绘?”
上大学前,叶晓彤对这个专业几乎一无所知。和很多人一样,她以为测绘就是“拿个黄色的三脚架在马路上量量”,很艰苦而且没啥技术含量。听完院士们的讲课,她对测绘的认识完全颠覆了。
从宁津生不紧不慢的讲述中,她第一次知道,原来“GPS导航卫星”“可量测的全景影像”,这些高大上的先进科技,和测绘这个古老的学科密切相关。测绘早已进入“大测绘”时代。
“测绘的本质就是研究时空问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干什么?要到哪里去?这既是哲学家问的问题,也是保安问的问题。同时,它还是导航研究的问题。”卫星导航专家刘经南常笑着给新生讲这个段子。
在他的课堂上,测绘这个看似枯燥的学科,不仅与哲学相关,与历史、生物甚至天文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信手拈来各种小故事:黄帝战蚩尤时三天三夜困在大雾中,多亏发明了指南车才打赢这一仗;因为有定位基因,人类才有方向感和距离感;用射电望远镜可以测量星系之间移动的距离,让我们知道宇宙是否在加速膨胀……
叶晓彤听得一愣一愣的,“很多完全没想到的地方,突然被启发到了”。这些院士仿佛是站在山顶上的一小撮人,他们的视线穿透远古和星空,顺着他们的目光,叶晓彤窥见了一个极开阔的地带。
这正是开这门课的目的。在宁津生看来,这些刚从高中毕业的孩子,不一定能完全听懂课,但他们会对测绘有一个“感性认识”,知道这个学科不再是传统的野外作业,它有很多高科技、很前沿的东西。
干过10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的他记得,开这门课前,很多学生不愿学测绘。虽然这所学校的测绘专业在全国排名第一,但每年录取的新生里,十个就有七八个第一志愿不是测绘,两三个强烈要求转专业。
卸任校长后,宁津生听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也是这个情况。他们尝试开了一门“院士课”,效果很好,转专业的学生少了很多。他很兴奋,和几位院士一商量,大家一拍即合。“与其靠辅导员去劝,去做思想工作,不如靠院士去讲。”
一晃,20年过去了。同济那门“院士课”早没了,武测合并到武汉大学,校名都没了,几位院士从中年迈入了暮年。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坚守在这门课的讲台上。

在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测绘三杰”与夫人合影,后排左起王之卓、夏坚白、陈永龄。
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
协调这门课并不容易。几位院士和教授,分属不同学院,且常有外单位院士加入,实际授课院士往往不止6位。听课学生多达上千名,需要分成好几拨儿。
龚健雅院士记得,武测与武大合校后,这门课受到很大冲击。武大有些领导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个事?”但宁津生很坚持,他一定要把这门课继续开下去。
“我们这6个院士,之所以对教学这么热爱,都是受到自己的老师的影响。”宁津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给新生上课,他有时会特意留出一页PPT,放上夏坚白、王之卓、叶雪安等老先生的黑白照片。
很多新生对这些名字并不熟悉。尽管他们创立了武测,后辈的研究成果飞上了太空,登上了珠峰到达了南极,但与他们的故事,却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1955年年初,身为同济大学副校长的夏坚白,呼吁创建中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
一年多后,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成立,同济大学等5所高校测绘师生随迁至武昌。刚从同济大学测量系本科毕业的宁津生,被分配至这所学校担任助教。24岁的他跨入校门时“有些失落”,他原本憧憬着去生产一线,“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这座新成立的大学,位于珞珈山南麓。原先是一片荒凉的坟茔,经过400多天的昼夜奋战,低低矮矮的山丘上终于冒出了几栋红砖小楼。
在这片简陋的校园里,宁津生彻底改变了人生志向。那些因测绘教育集聚于此的教授们,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那些教授,老人眼中放出亮光。
这所新学校拥有5位一级教授,数量在整个湖北省首屈一指。其中多位曾任著名大学校长:夏坚白曾在解放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王之卓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金通尹曾任北洋大学代理校长,陈永龄曾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另一位一级教授叶雪安,曾是中国第一个测量系的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带着同济测量系师生,拖着笨重的仪器,一路逃难一路讲课。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教授们努力保住一块教学的讲台。首任院长夏坚白极力主张“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在他的倡导下,所有一级教授都亲自给新生上课,包括他自己。
教授之间相互听课评价,这是建校时便创立的制度。夏坚白常穿着胶底鞋,悄悄出现在教室中。
教师上台讲课,被视为一件颇为神圣的事。在开学前,王之卓总会将一学期的课程全部备完,写好讲课笔记。讲课前一周,再修改补充,考虑教学方法。到了课前的那天晚上,再把第二天所讲内容全部仔细备一遍。他的讲课笔记由于多次补充,写得很乱,别人看不懂。
作为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宁津生必须先从助教干起,除了为讲课教授画挂图、批作业、给学生答疑外,他还得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听教授们上课,学习怎么教书。3年后,他才有资格登上讲台。
宁津生记得,那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很近。每个星期,老师会到学生宿舍答疑,因为学生多,“往往一两个小时的课程,答疑时间就有六七个小时”。野外实习时,师生更是形影不离,吃住都在一起。
如今“院士课”上的多位院士,都在这个时期考入这所大学。和现在的大多学生一样,测绘并非他们的第一志愿。
测绘界唯一一位两院院士李德仁回忆,他当时也有很大的专业情绪。这位尖子生原本报考的是北大数学物理系,“想搞火箭”。没想到,教育部为了照顾这所新大学,将他录取至武测航空摄影测量系。听了夏坚白院长的新生训话,以及系主任王之卓的讲课,他才逐渐喜欢上这个专业,“发现也需要学好数学和物理”。
他喜欢琢磨问题。对一位苏联专家撰写的教材产生质疑后,他写成论文递到已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手中。没过几天,王先生将李德仁约至家中,两人坐在书房里,久久地讨论,直至天色已晚。之后,李德仁成了王先生家的常客。正值困难时期,老先生家每每分到东湖鱼、梁子湖螃蟹之类的好东西,总会叫上学生一起享用。
原本想学生物、打算回去复读的刘经南,在入校后也慢慢对专业来了兴趣。上叶雪安讲授的大地测量学时,他发现课本中一个定理的推导过程“不严谨”,它借助了图形思维,而不是“完美纯粹的数学思维”。刘经南一头扎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资料中,自学了理科的微分几何、复变函数和矢量代数,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纯理性、抽象的思维推出来”。
过了一个学期,在宿舍楼的答疑室里,刘经南将好几页的推导纸递给叶雪安。这位60多岁的老先生,叼着烟,仔细看了刘经南的推导,高兴地说:“你这倒是个严谨的方法,我们都要借助于所谓的微分线段,你这个完全不借助图形,从理论到理论。你这个小子不错。”
刘经南很受鼓舞。他问:“这个可以发表吗?”叶雪安悠悠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文章没能发表。“文革”很快袭来。被抄家后,叶雪安因不堪凌辱,在浴室中服毒自杀。武大图书馆中几本发黄的教材,是他留下的不多的痕迹。

5年前,宁津生80岁寿辰时,6位院士合影,左起张祖勋、刘经南、宁津生、李德仁、陈俊勇、龚健雅。
夹着烟纸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教材
1968年冬天,包括刘经南在内的高年级学生已全被分配或遣散。很多人流着泪烧掉专业书,王之卓却给大家打气:“哪怕将来我们去卖冰棍,冰棍箱子里也要带上书。”
学生走远了,他和夏坚白仍在挥手:“不要丢了专业,不要丢了外语!”不出两年,武测被撤销,军队接管了校园。
1972年春,政治环境略有改善,夏坚白找来武测一位前同事,共同拟就一份近5千字的建议书,恳请“恢复武汉测绘学院、测绘科学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听说一位前同事打算调去地震队,夏坚白拉着他的手说,“叶先生(指叶雪安——记者注)死了,搞大地测量的人不多啊!你不要走,武测会恢复的,是需要你们的。”
1973年3月,周总理终于作出批示恢复这所学校,夏坚白闻讯后热泪盈眶。但他再也没能踏上讲台。
在师生流散的岁月里,他曾将几位原武测教师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测绘科学研究小组”,匿名翻译了两本外国学术著作。宁津生冒险加入了小组。
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编写教材。文革结束后,他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小包,里面是一叠各种颜色的纸张,夹着游泳牌和飞马牌香烟的烟纸。这些写满公式和符号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摄影测量原理》。
早在留学德国时,夏坚白、王之卓及陈永龄就约定:回国后要合力编写教材,“一同做一番事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测绘学博士,曾靠“中英庚款”一同辗转英德留学。学成回国后,被称“测绘三杰”的他们,在战火纷飞中靠着书信,合作编出了中国第一套大学测绘教材。
宁津生和几位院士接过了老师的事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讨教材的修订。20年间,《测绘学概论》再版了3次,变成了150多所高校的专业基础课本。

王之卓(中)、李德仁(左)、龚健雅师生三代院士合影。
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李德仁常提起导师王之卓。
这位学部委员曾亲自为李德仁改论文、排章节,将他的论文推荐发表,而且从不署自己的名。出于政治原因,研究生入学考了第一的李德仁,未被录取。文革结束后,王之卓立即将这位学生召唤回校,为他举行专门考试。干过建筑工,种过水稻,扎过钢筋的李德仁,终于在39岁回到书堆中。
靠着老师坐公交去邮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荐信,李德仁飞向了更远的学术世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学位。324页的博士论文,取得该校历史最高成绩,评委评价“它解决了一个百年难题”。
有不少外国研究机构挽留他。妻子给“老大不小”的他寄来书信: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花国家的钱,你还不如一头牛呢,到现在都没挤出一点奶来,现在到了该回国“挤奶”的时候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李德仁回到了老师曾站过的讲台上。
和导师一样,李德仁一心扑在教学上。他一口气给本科生开了3门课,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还编出3本教材。
但变化也在一点点发生。评上院士后,李德仁眼瞅着研究经费翻了又翻,原来是几万元,后来小数点往后挪了几位,涨到几千万元。他越来越忙,各种会议、出差,将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
当了武测校长后,他离讲台更远了。一位本科生毕业后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写信给李德仁的夫人说,从没听过李院士的课,深感遗憾。李德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接过信后,他心里“很不好受”。
他亲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学生所在单位,给所有员工讲了一堂课。
刘经南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每晚仍坚持去实验室。很多人摸清这个规律后,在门口排着长队等他。能留给学生的时间少之又少。
宁津生认为,校长没空上课可以理解,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把握方向、服务教师”,归根结底是提高教学质量。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长,现在甚至连很多最普通的教师,都很难把教学放在首位。决定他们晋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课,而是一堆堆的论文、表格和项目。
“这个评价体系很糟糕,会把高校的教学拖垮。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这位老校长提高音量说。他怀念起刚进大学的日子,那时所有新教师从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许多大学,博士后进大学直接就是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也淡了。去很多新建的大学城参观时,刘经南感触很深。那些大学都在郊区,修得很漂亮,教室很大气,但一到晚上,就变成了死城,“看不见一个人”。老师都回到城内,学生窝在宿舍里玩游戏。
“感觉老师和学生脱节了,学生变得很孤独、很内向。”刘经南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
这些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院士课”的诞生。几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讲台。

2017年10月12日,宁津生给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第一讲。
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20年来,这门课更新的速度很快。讲地理信息系统时,龚健雅以前常讲“单机的、局域网的系统”。而现在,课件上的内容早变成了“广域网的、手机的系统”。
与课程的发展同步,中国科技界也在大跨步向前。李德仁记得,刚回国时,45岁的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把文革丢掉的时间补回来?”当时在武测,除了上课,每个学者都在“玩儿了命地做科研”,半夜翻墙上机是常事。
如今,科学界早已翻过新篇,到处都在谈论“创新”,谈论“国际一流”。但到了新时代,宁津生却不鼓励学生“动辄提创新”。“搞两三年就让你们创新,创国际一流,不现实。还是要踏实一点。”他常对学生说,“从0到1的创新很难,你们作为学生,可以多尝试从1到1.5的创新。”
刘经南的教学风格不同。这位“喜欢挑战”的科学家,思维发散开阔,他常在课上坦言自己的“诺奖情结”。第一次见面,一位博士生就被他的气势震住了。导师坐在桌子对面,语气很平常,但决心毋庸置疑:“你们要做,就做到国内第一、世界第一。”
李德仁则认为,创新源自学科交叉。这一看法,与他的导师一脉相承。王之卓曾打趣地提出“科技边际效应观点”:“不同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效应,正如大陆与海洋的交接边缘,一定是生产力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样。”
不过,不管如何创新,几位院士都认为,做科研必须坐得住“冷板凳”。早在武测院刊创刊号上,王之卓就直言:“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一个较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宁津生一辈子专注于研究地球重力场。为了做一个课题,他和合作者一道一道解开了130321个公式。学生李建成花了26多年时间,将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提高到厘米级。46岁时,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
从中学时代起,刘经南就在琢磨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得诺贝尔奖?”大学时他想到,如果能计算出宇宙膨胀的加速度,离那块金灿灿的奖牌肯定不远了。当了博导后,一个“性格有些坚毅”、来自农村的陕西男生接受了这个挑战。刘经南激励他,“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么容易的,你可能搞不出来,但你可以让你的学生继续搞,徒子徒孙都可以做下去!”
好几年时间里,这个学生一直在埋头编软件,一页一页地啃英语论文。交流科研进展时,刘经南发现,他抱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是一句句的汉语翻译。
没过几年,3位美国教授宣布,测出宇宙以正加速度膨胀,这个力来自暗能量。2011年,这一发现获了诺奖。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刘经南讲到了这个故事,多位学生对此印象深刻。虽然与诺奖无缘,但这个“傻得可爱”的陕西男生,后来将同样的理论方法,用到了嫦娥号的数据处理上。
在这门课上,刘经南好几次预测与测绘相关的诺奖。3年前,他正坐在汽车里,一个学生兴奋地打来电话,“你讲的生物导航系统真的得奖了!”
20年来,几位院士努力在学生心中撒下一种渴望,那就是对科学高峰的向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提醒着,这种渴望不能被扭曲、被异化。这一教诲同样来自老前辈们。
王之卓极力反对过分溢美之词。但凡有人在文章中提到“王之卓公式”,他阅稿时总要划去,附上纸条,“请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
龚健雅曾将自己的一个数据结构命名为“perfect data structure(完美数据结构)”。王之卓看过论文后严肃批评道,“你不能自封为完美的。”龚健雅解释,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完整的”。老先生皱了皱眉说,还是不行。
指导博士生李彬时,宁津生也有着相同的态度。一次,这位学生打算用“前沿、首次”几个词介绍自己的最新算法,宁津生果断否定。他送了一幅毛笔字给李彬,上面写着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严谨求实。

2017年10月12日,讲课完毕后,宁津生给同学们签名。
要是因为退休,断了这门课很可惜
没成为宁津生的学生之前,李彬觉得宁津生就像“遥远的一颗星”。在一个高端学术交流会上,李彬远远望见这位院士、前校长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
成了他的博士生后,两人经常隔着一张小桌子,从科研聊到细碎的日常生活。每次离开老师家的小客厅,李彬包里总会被师母塞得满满当当,里面有豇豆、花生米、辣椒酱等各色“宝贝”。这位博士结婚时,宁津生穿着衬衫西裤出现了,做了他的主婚人。
还没等他毕业,老师突然“老了”。他的腰折了下去,走路久了便心慌腿软。来参加李彬的论文答辩时,老人在秘书的搀扶下走来。在场的评委都劝宁津生回去等消息,但他坚持听完3个多小时的答辩。
给本科生讲课时,宁津生也很难再站着上课。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院士不得不“服老”,上课时坐在一把灰黄的旧椅子上。
但他们仍在为这门课忙碌着。教材的第4版正在修订之中;同样的概论课移植到了同济大学;最近,给研究生开一门类似的概论课,又被列入计划之中。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领导来到武汉大学,征求院士们对70岁退休制度的意见。宁津生在会上平静地说,他对退休没有意见,只有一件事,还望商榷。
这位老科学家顿了顿说,他想继续给大学新生上课。“我们6个院士有5个过了70岁,要是因为退休,断了这门课很可惜。”
正如当年老教授用精彩的讲课留住了他们,这几位院士也留住了许多年轻的学生。宁津生记得,开了这门课后,转专业的学生少了很多。到了第三年,头一遭有外专业的转进来。
在和时间的角力中,几位院士最关心的是人才的接力。
在李德仁眼中,导师王之卓是个真正的“教育家”。这位院士培养出了3位院士,除了讲授《测绘学概论》的李德仁和张祖勋,还有被媒体称为“高铁院士”的刘先林。
刘先林是李德仁的同班同学。最近他突然在网上“火了”,一张照片广为流传:一个光脚穿着旧皮鞋的干瘦老头,埋头在高铁二等座上修改演讲稿。在测绘界同仁眼中,刘先林“不修边幅、不善言辞”,但他是个“奇才”,一个人鼓捣出了5种航测仪器,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德仁很钦佩这位同门兄弟,但他还是向刘先林提议,要培养年轻人。“老刘,你这个老牛能活多少年?你刘先林死了以后,刘先林的东西没有了,你不是成功的。”
刘先林有些触动,点了点头。
同几位老先生一样,6位院士都将学生视为自己的最大成就。宁津生和李德仁门下,各出了一位院士。如今,他们也踏上了接力之路,踏上了这门课的讲台。
原标题:武大一门课6位院士共同讲授座无虚席,被称“最奢侈基础课”
编辑: 陈晓怡纠错:1719646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