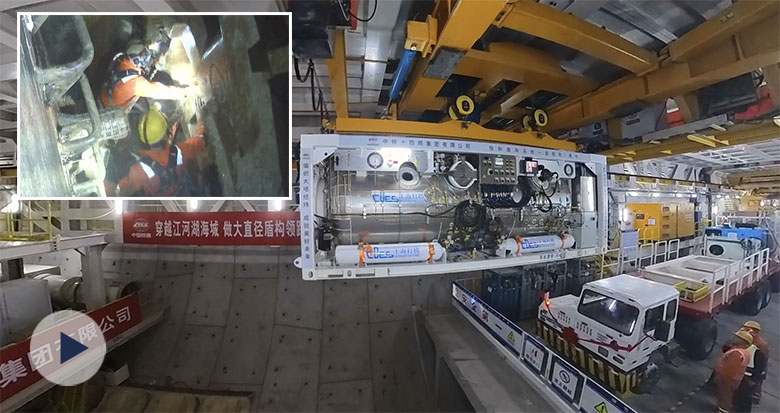舒俊陶的2020年,是在集盒广场一场热闹的街舞圈Hip-Hop跨年派对中到来的。
音乐伴随着每一次呼吸和心跳,点燃年轻的身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他在拥挤的人海中轻叹了一声:“真的30岁了呢。”
出来已是元旦凌晨2点多,三江口楼群的流光溢彩已落幕,狂欢后的人群渐渐散去,街道又回到了平常的样子。最好的兄弟一把揽过他的脖子:“今天我就回老家了!”
“走吧!走吧!”舒俊陶挥挥手,嬉皮笑脸地哼下去,“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你呢?”好朋友转过脸看着他,“想好今年到底要干什么了吗?”
舒俊陶眯起眼睛:“我想想啊!”从小到大,这个问题他被问过无数次。当年一事无成的小混混,现在已经是圈内有名的B-boy(街舞男孩)、YY直播平台签约金牌艺人,上过三次央视《星光大道》。这个90后的故事,或许会让许多曾经不知道要干什么的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影子。
叛逆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父亲把舒俊陶没考好的卷子扔得满天飞,盛怒之下青筋直暴,“旷课、逃学、离家出走,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那年舒俊陶14岁,在宁海读初中。这个瘦弱少年看着父亲握紧的拳头,心里盘算着:真打下来,要不要还手。
父亲没有动手,只是颓然坐下:“已经换了好几所学校……”
舒俊陶一声不吭,他也委屈:小学时喜欢打篮球,一心想进校队,哪怕中午只有40分钟休息时间,也要在午饭前挤出15分钟去打一圈,但不管怎么努力,永远是陪练,直到毕业他才知道,是父母怕影响学业不让他进。
“他们也是为你好!”体育老师当时抱歉地笑着,“本来你的条件是数一数二的。”
正是叛逆的年纪,他开始反抗。学校不让留长发,他偏留,校长打电话给家长,父亲开车把他送到理发店门口:“要么剪,要么滚!”他一推车门,头也不回地走了,用兜里仅有的几元钱打电话给一个同学,两人在街心的小公园里开了几瓶啤酒,度过了第一个离家出走的夜晚。
打那以后,头发变成了父子之间战争的导火索。舒俊陶不记得有多少次,父亲气急败坏地把他从网吧拎出来,直奔理发店,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剪短一点,越短越好!”
反抗无效,逃学成了家常便饭,交了一帮社会上的朋友,成绩一落千丈。父亲无计可施,忍不住咆哮:“你想干什么?你说呀!”
舒俊陶真正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是在看了一场名为《精舞门》的电影之后。那时他在甬江职高读表演专业,还是厌学、逃课。影片中陈小春的街舞第一次让他感觉到那种热血沸腾的力量。
宁波找不到合适的老师,他打听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有街舞专业,对父母说,无论如何都要去。
幸好那所学校当时不算难进。舒俊陶记得很清楚,父亲把他送到北京,在宿舍安顿好,对着窗外的夜风叹了口气:“你做什么都是3分钟热度,这次至少把文凭拿到。”
他知道,这是父亲的底线了。

热爱
“要辞职?”父亲捏着舒俊陶的策划书,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不上班你想好干什么了吗?”
那一年舒俊陶24岁,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朝九晚五,收入尚可,但他不喜欢这份工作。“我还想跳舞,”他小心地看了父亲一眼,赔着笑,“我还想问你借点钱。”
父亲瞪着儿子,发现儿子已经比自己高了半个头,手臂肌肉结实紧致,突然意识到:这个从小不省心的孩子,已经很久没让他操心了。
进大学后,舒俊陶变得很勤奋:下午上课3小时,晚上练习3小时,他总是去舞蹈房最早、离开最晚的一个,回宿舍后再看视频讨论学习。此外,他每天做250个仰卧起坐、250个俯卧撑。一年下来,体重从107斤升到130多斤,小瘦子也有了马甲线。
脱胎换骨,是因为找到了真正的热爱。
大学最后一年,老师带着他们备战一年一度的BIS世界街舞大赛,每天都练到昏天黑地、动弹不得,回宿舍一头扎在床上,却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睡不着。这是舒俊陶第一次这么投入地去做一件事,憋了全身的劲儿,太想得到一个肯定。
那一年BIS大赛,舒俊陶和队友进入了四强,是唯一的中国团队。他们在热泪盈眶中告别大学,并且约定:以后一年一聚,参加每一年的BIS大赛。
但后来老师离开了中国,散落在全国各地的队友再也没有聚起来。
舒俊陶开始按部就班地上班。最初的时候,他每天一下班,就从七塔寺旁边的公司出发,戴着耳机一路踩着舞步去天一广场的练功房,练舞到深夜。后来工作地换到了宁海,他就赶在周末到宁波市区来练两天。再后来,越来越忙,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渐渐放弃了。
舒俊陶发现自己胖了,镜子里,脸大了一圈,满眼都是疲惫。他问自己:就这样下去吗?
2014年4月22日,他把这个日子视作人生的转折点。以前一起跳舞的朋友来看他,他们在嘈杂的小饭馆里吃夜宵,一边喝酒一边抱怨,浙江Hip-Hop文化氛围太弱,真要去参加比赛,都找不到人。“为什么不自己建个团队,做Hip-Hop推广呢?”那句话脱口而出时,他看到朋友眼里的光,感觉有个东西在胸口东奔西突。
那个沉醉不知归路的晚上,他做了辞职的决定:“我要继续跳舞!”
“那你怎么养活自己呢?”父亲怀疑地看着他,“做舞蹈老师吗?”
他说想好了,组建一个专业团队推广街舞,未必人人都是专职,但是等宁波有了这样的文化氛围,就可以通过活动和培训赚钱。
他没什么积蓄,想向家里借个一两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他在网上百度了一份项目策划书模板,磕磕绊绊地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去,交给父亲。“什么乱七八糟的,”父亲嫌弃地打开,皱着眉头读完,“写得真是烂,不过想法倒是有一点。”
舒俊陶看到父亲嘴角一丝浅浅的笑意,知道他已经答应了。
直播
舒俊陶在家宅了好几个月,每天打打游戏看看书。 “休息休息也好,”父亲说,“不急,等你想好要做什么了再做吧!”
那年舒俊陶27岁。辞职创业两三年后,他的团队已经扩张至50人,完成了一系列Hip-Hop演出、赛事、培训以及地下文化节。公司走向正轨后,舒俊陶在YY直播平台开启了主播的新身份,希望打破地域限制推广Hip-Hop。
那时候,直播市场在各路资本蜂拥之下迎来爆发期,“千播大战”时代到来。更“刺激”更“劲爆”的内容充斥着小小的屏幕,很多人评论说:“跳舞有什么好看的!”还有人直接让他滚。
队友也很排斥:“你以为唱唱跳跳就会红吗?”
舒俊陶在意每一条评论。他看别的网红,琢磨他们每个段子和每句话,又觉得有些东西学不来。熬红了眼睛,夜以继日,到头来发现,只是感动了自己。
他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失去信心的,感觉好像一下子被掏空,连舞也不想跳了,成天无所事事地宅着。
转机出现在2017年底,YY平台邀请他参加了当年的年度盛典。2018年,舒俊陶通过面试成为YY造星培养梯队中的一员。平台为他量身定做了个人单曲《感觉爱》,抖音上架的当晚,使用量就近万,接着得到了上央视《星光大道》的机会。
这是舒俊陶第一次上电视节目。YY经纪总监亲自上阵,3个执行经纪从面试开始全程陪伴。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毕业前那段起早贪黑竭尽全力的日子,舒俊陶在忙碌之中来不及去想:“为什么是我?”
几个月后,当他从《星光大道》的周赛、月赛一直走到年度嘉年华,才慢慢意识到,被选中只是因为才艺。直播行业到了洗牌的时候,网络监管越来越严厉,平台开始分梯队培养正能量、积极向上的艺人,他这样“只会唱唱跳跳”的主播,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
上完《星光大道》后,涨的粉并没有想象中的多,但这段经历对舒俊陶来说意义非凡。他看着父亲在电视机前咧着嘴、有点手足无措的欢喜样子,心中感慨万千——多年来不被理解的青春,此刻终于得以正名。
长大
一转眼,2019年也过去了。这一年,YY培养的顶级主播摩登兄弟举办了3场万人演唱会,跻身演艺圈一线流量行列。人们讨论得更多的是李佳琦和李子柒。
但传奇总是极少数。据《新京报》报道,仅有21%的全职主播月收入超过万元。舒俊陶很幸运地就在其中,但并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高。此外,超七成主播表示每天三餐无法按时保证,93.9%的职业主播在法定节假日也要直播。
2019年底,一个朋友决定退出B-boy团队回老家,因为父母催他买房找对象。舒俊陶完全能理解,梦想在现实的齿轮里慢慢磨,渐渐面目模糊,很多人在一场痛哭或宿醉后,走上一条安全的道路。
舒俊陶出了第二首单曲《差不多的歌》。他没有摩登兄弟那么大红大紫,但一步步稳扎稳打,喜欢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每天直播两次,加起来七八个小时,这意味着每天都要准备很多内容:唱歌、跳舞、脱口秀,各种与粉丝、游客互动的段子……前有大牌主播做“天花板”,后有层出不穷、不停追赶的新人,舒俊陶几乎全年无休,害怕一放松就会掉粉。
有回太累了,洗了个澡就睡着了,头磕到浴室水泥地上。他在直播中聊到这段经历,没想到很快母亲就打来了电话,问他有没有事,说“别干了,太伤身体了!”原来母亲不但注册了一个小号在看他的直播,还拉上了外婆,遇到不客气的网友,还会帮他怼回去。
舒俊陶心里五味杂陈,当年的叛逆少年早已和岁月握手言和,但依然不是个听话的孩子。
90后这一代人,一出生就能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他们更愿意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尽管未必轻松。
舒俊陶觉得,在互联网世界,每个人都像茫茫大海里的一个孤岛,想要“被看见”,就必须成为某个领域的超级ID,而方法只有一个:更勤奋、更专业,不拼不行啊。
他已经想好今年要做什么了。“也许精力会从直播
转向短视频,但总不外乎踏踏实实推广Hip-Hop、踏踏实实做内容。很多人都觉得,年轻人喜欢的是轻浮的、流量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其实不是的,内容够‘高级’,他们就喜欢。”
舒俊陶在参加街舞圈跨年派对的时候,B站的跨年晚会收获一片好评,被称为“最懂年轻人的晚会”。他后来也去“补了课”,身边有80后、70后,晚会上那些玩笑中的正经、狂欢中的热泪、鬼畜中的深情,分明可以打动所有人。
新年零点,B站跨年晚会上,五月天唱起《倔强》。这首老歌发行于16年前,那时舒俊陶还是一个常常逃学,不知道干什么的小混混。如今,听歌的孩子长大了。宁波晚报记者樊卓婧
编辑: 陈奉凤纠错:171964650@qq.com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