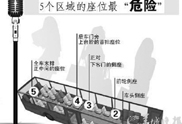鄞州高桥"最美丈夫" 30年携妻上班书写爱情传奇

余训华将老婆背上车。

老婆上下楼,都是余训华抱的。
2青春被命运撞了一下腰
余亚飞在刚生完儿子的时候被命运撞了一下腰,那年她26岁。
从月子里起,她觉得腰痛、腿又麻又胀,痛了两个多月,医生说啥毛病也没有,贴点药膏就好。
她也不敢请假,领导说她活干得好,正在提拔做“当班师傅”的当口。
她一边坚持上班,一边自己吃止痛药,找赤脚医生打止痛针,直到有天晚上痛得昏了过去。
送到宁波的大医院时,不知道做了多少检查,余训华只记得,最后一个医生感慨了一句:“唉,怎么这么年轻。”
“这么年轻怎么了?”他的脑子里嗡嗡作响。
余亚飞被确诊为“脊椎脓肿”,医生通俗地解释说,就是脊椎里有一些东西在慢慢腐烂,后果就是下肢慢慢失去知觉。
病情恶化比预料得要快,住院的那天,余亚飞只觉得下肢麻木,第二天那种麻木已经蔓延到腰部以上。
她大哭,泪水顺着脸颊渗进头发里,头发都结块了。
恐惧像一条毒蛇紧紧缠绕,隔了这么多年,余亚飞依然能够回想起那种感觉,好像身体的每一个零部件,无论是能动的还是不能动的,都是僵硬的,都不再是自己的了。
“不要怕,会好起来的。”守在病床边的余训华笨嘴拙舌,只会说这么一句话。
余亚飞边哭边骂,她知道好不了了,更糟糕的是,她发现自己不会大小便了。
余训华还是不太会哄人,有点着急,半天挤出一句话,那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插导尿管呀,大便我给你抠出来。后来他真的戴上手套,蹲下来,一点一点地给妻子抠大便。
“我哭都不好意思哭!”余亚飞把头缩到被窝里。她看不到丈夫的表情,也不敢想象。
余亚飞的母亲后来也给女儿抠过大便,不过通常用的是筷子,只有余训华,坚持用手。他坚持了一年多,直到妻子渐渐有所好转。
医生说,不能断定余亚飞的病和生育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个男人心里一直有一个结:“她好好地嫁到我们家来,生个孩子就这样了,说到底总是因我而起的,我不对她好,说不过去。”
作为一个男人应该负责,蹲下来照顾妻子,余训华觉得这是一个丈夫应有的姿态。
3风雨过后太阳照常升起
余亚飞在医院做了手术,出院的时候,背上多了条一尺长的伤口,下肢恢复了部分知觉,她可以扶着椅子站起来,但是再没有办法挪动一步。
丈夫去上班了,那会儿他的工作已经变成了开运输船,不能常回来。儿子给婆婆养,她的母亲一边照顾她一边还要忙地里的活。
她是个要强的人,想去解小便了,没人在身边,就自己扶桌子椅子,扶着墙,一步步往厕所挪,但最终还是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尿了一裤子。
母亲回来后,两人哭了一场。但丈夫回来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说。
有一阵地里忙,余训华怕岳母没时间做饭,每天早上为妻子做好午饭,用保温杯温着。她有一次不小心,把保温杯打碎了,饭菜溅了一地,眼睁睁地看着却什么也做不了。
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母亲一直没有回来。余亚飞饿着肚子等,直到饭菜变得冰凉,在泪眼里模糊、扭曲———自己收拾不起来的岂止是打碎的饭菜,还有家,孩子以及今后都无法独立行走的人生。
傍晚,余训华回家看到这情景,眼圈红了。他说:“没有腿,有我。我背着你一起上班。”
“那怎么行?”
“没关系的,本来你也无聊我也寂寞,一起上船正好作个伴。”
就这样,余亚飞上了船,余训华到哪儿都把她带着。那个狭窄昏暗,人都站不直的船舱,成了流动的家。两个人挤在1米宽的铺上,生煤球炉子做饭,船上风大,常被熏得眼泪直流。最麻烦的是雨夜,那时的船舱经常会漏,被子全湿了,夫妇俩只能把所有衣服都裹在身上,坐着等雨停。
随着雨水一起到来的,还有余亚飞下肢的疼痛,在船上的漫漫长夜里,她总是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腿,这样会好受一些,余训华也会帮着一起敲。敲着敲着,一夜就过去了,太阳还是照常升起。
两人呆久了,也没什么话说,周围只有水流的哗哗声。余训华觉得太安静了,怕妻子又多想,就说,你唱唱歌吧,你以前不是喜欢甬剧吗?于是余亚飞重新拾起这个久违的爱好。把那些经典曲目又翻了出来,时间就过得快一些。
漂泊的生活总算有点了诗意:晴朗的傍晚,船靠了岸,他生火做饭,她唱起了最喜欢的《半把剪刀》:“我不想山珍海味绫罗袄,只求青菜淡饭粗布衣……”
炊烟在空中散开,余训华的笑容模糊而温暖。他觉得妻子唱得比收音机里的还要好,那也是他当时唯一的“娱乐节目”。
许多年以后,余亚飞因为多种并发症,身体逐渐恶化。一次住院前,她在丈夫的手机里录了自己唱的甬剧:“我要是不在了,你听听这个,也是一样的。”
余训华用力眨着眼睛,好像是为了不让眼泪掉下来:“那哪能一样,你要好好的。”
| 图片新闻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