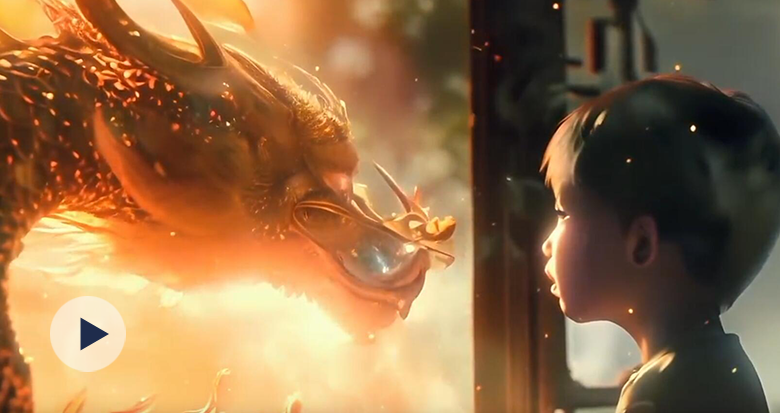中国宁波网记者 车君斐
自我记事起,每年的大年初一,都要到祠堂祭祖。而幼时的我,回祠堂的路隔着一千三百公里。因父母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跟着招工的南下深圳打工。
外婆是海曙区石碶镇车何渡村人,经常回娘家,还把第二个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托给了村里的手艺人拜了师傅。父亲家贫,爷爷差点将最小的两个儿子送了人……兜兜转转,我算得上正宗车何渡人。
在深圳异乡,我们是“北佬”。年年春运,战线绵长。在那个年代,工资条还是手写的纸条,接打电话要靠腰间别着的BB机。火车票,只能在发售的车站,透过那一格格小窗口,一手递去仔细清点浸着汗的钞,一手接来带着希望的一小张车票。
没有实名制的时代,买车票靠人工排队。在开售日前两天,凌晨半夜就会有不少人带着板凳簇拥在窗口前。2000年开始市政府专门调用了体育馆作为发售点。父亲有时下了班会去弯一圈看看,望着铁栏杆层层绕绕的人群,希望终是次次落了空。和黄牛交易,是不是办法的办法。虽说这价格会随着行情上下浮动,但这区间一般在翻倍与翻一倍半之间。有时不只是花钱,黄牛还会卖假票。有时这价格实在太高,高到那一年我们买了飞机票。
买定了票,母亲会将深圳的出租屋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所有的器具擦拭折叠收纳。除了家务还需采购,每一年的新衣新鞋,为村里人代买的药物,坐火车要过夜,最期待平时没机会吃的方便面。到了坐车的那一天,心中弥漫紧张、期待等种种复杂的情绪。大包小包背上身,行李箱的滚轮,在夜色中发出骨碌碌的声响。辗转交通,常见瘦小的男人女人淹没在巨大、最能装的蛇皮口袋间。绿皮火车拉响汽笛,蒸汽滚滚,走下站台不自觉地加紧脚步。若是深圳始发,我们常要在杭州周转。有时买不到火车票,便要出站购汽车票。漫漫征途,抵家的那一刻才算结束。

父亲作为家中最小的,总会不自觉受到些偏爱,年年的大年初一,我家总是最后一名到的祠堂。连日的赶路和紧张焦虑,在故乡的土壤和亲人溢于言表的热情招待中瓦解殆尽。
从出生就被带到深圳,一时间面对认不清的亲人的脸,听不懂的故土乡音,眼前的景象从炫目璀璨的高楼大厦到总飘着小雨的田间地头。我不懂父母自然而然融入的仪式,纸制银元宝焚烧后的烟雾萦绕着点点烛火,从心底里抗拒烧香跪拜。祖宗?阿太?在我心里毫无概念。爷爷在父母婚前便已离世,奶奶在爷爷离世后重重忧患之下失明,也在我懵懂之时离去。
直到我成年很多年后,才后知后觉觉出味来。爷爷奶奶没得早,但也毫不妨碍父辈的兄弟姐妹们团结一心紧紧依靠,千辛万苦也抵挡不了回乡的心。现时生活条件好了,即使安排了春节出门游玩,也一定要早早来祠堂祭拜,才能踏上旅途。年年的中餐晚餐,大伯伯一定会热情安排到村口他家一聚。父辈们在温暖黄色灯泡的映照下划拳喝酒,脸红脖子粗,热闹喜庆的氛围洋溢在一盘盘佳肴中。
车家的祠堂,几经风雨。我从未在这个村宿过一日一夜,但它串起了外婆、母亲、父亲的年少和故乡情。
编辑: 杨丹纠错:1719646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