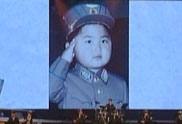石塘下的别样风景

“又去石塘下了?”看到我空间中的图片,好友们习惯这样问。
去那里拍照,没有一次让我空手而归的。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不同的场景,总会让我有不同的收获,回来整理这些照片时,那些真实的生活记录让我有如获珍宝的喜悦,鲜活的画面重又展现在面前,那些没有受到惊扰的人们本色出演,丰富着一帧帧照片、一个个画面。
一个熟悉的朋友调侃,说我对着一堆破砖、一个垃圾桶可以拍上半天,那里大多数的房子已经被拆,我喜欢去那里,我觉得那里残存的低矮屋舍比起那些高楼大厦来更适合进入我的中焦镜头。
城镇的边缘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清晰的是一墙或是一路之隔便是分界,那边是齐整的高楼,这边是低矮的破旧小屋。而穿梭在其中的人们又模糊着这种界限。早上,他们从这里出发,往城镇打工;晚上,又匆匆返回这里——他们用作栖身的家。高楼里面的人们或许不惧风雨,活得靓丽、过得光鲜,小屋里面的人们也有他们各自的人生,在蜗居里演绎甜酸、品尝苦辣。
住在那里的大多是一些外地来镇打工的,在这样简陋的地方居住,贪图的无非是那里相对低廉的房租,水电费不算,一百五、两百一月的房租,只是一个容身之处,却在有限的收入中实实在在节省了一点开支。他们基本不去镇上的菜场买菜,旁边有些小菜摊,早晚两市,肉类、鱼类、蔬菜,没有高档菜肴,但基本能满足每日饮食所需。
在屋舍与瓦砾的空隙处,勤劳的人总能开辟出属于他们的田园,花菜、菠菜、卷心菜、莴笋……齐刷刷,绿油油,是小屋前的亮丽。看得出经营这些菜园子人们的用心,一来贴补了餐桌,而开门见绿,也赚来每天的好心情。吃不完了,腌了晒了,储存起来。春夏之交,就经常能看到就地搭起的架子,晾晒着吃不完的腌菜干。
晴天的时候,那满架的衣衫被褥,花花绿绿地点缀其间,像旗帜一样随风招展,空气中飘着皂液的清香和太阳光的味道。阳光毫不吝啬地惠施,从不厚此薄彼,主妇们总是心怀喜悦洗洗搓搓、晾晾晒晒。
去过多次,像样的房子一次比一次少。原先给我印象深刻的那幢外墙满是爬山虎的小楼也拆了,那里住着一位健谈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石塘下人,她说那些绿萝让她的小楼冬暖夏凉,还托我多给她的小楼拍些照片。这一次,我带了小楼的照片给她,但她的小楼已经拆了,老人也搬走了,绿萝也不见了。
我喜欢到那里拍照还有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人总是那么友善,毫无厌烦戒备之心,或许,为生计奔忙,他们根本无暇顾及你的存在,于是,原生态的生活场景才一次次被定格。去的次数多了,我们也会闲聊,我是不善谈的,但他们似乎从未把我当外人,所以每次都会聊得很轻松,让我感觉自己非旁观者,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
好几次遇到捡旧砖的在那片废墟上淘着有花纹或字迹的旧青墙砖,而我也乐于像那些捡旧砖的人一样,在城镇边沿的旮旯里捡拾着被城镇遗落的碎片,生活的碎片。
终有一天,这里将夷为平地,代之以新的高楼。(王晓晖 文/摄)
| 图片新闻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