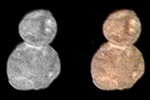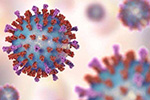中国宁波网记者张璟璟 金鹭

(2020年1月3日,宁波科协人员慰问孙院士)
记者刚刚获悉,今天上午8:50,甬籍中科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孙儒泳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逝世,享年93岁。
“没想到这次新春慰问,真成了与孙院士的永别。”宁波市院士服务和咨询中心夏科长告诉记者。
春节前夕探望院士是宁波市科协的传统。今年1月3日,科协工作人员前往广州,探望了正在华南师范大学 (石牌校区)校医院住院的孙儒泳院士。
“虽然行程紧张,但得知孙院士身体状况不太好,还在住院,领导让我们务必去探望。”夏科长说。

“院士助理提前把我们要来的消息写在本子上告诉院士,他一大早就拿着本子在等我们,真的让人感动!”夏科长回忆道,当时孙院士已经不会说话,但思维还是清晰的,“我们向他说起家乡的发展情况,他虽没有说话,但频频点头回应。”

孙儒泳院士,1927年6月生,曾就读于宁波四中,195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1958年获苏联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0年宁波四中165年校庆上,孙儒泳院士作为校友代表发言。资料图)
孙院士常年从事生态学教学和科研,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共16种,所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获第二届高校教材评审全国优秀奖和1992年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
“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优势只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是孙儒泳院士对自己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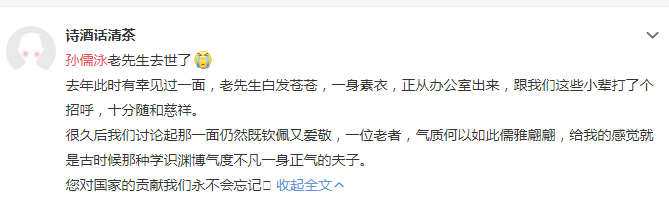
(网友缅怀孙儒泳院士)
相关报道
2012年9月24日,《中国科学报》刊登一篇对孙儒泳院士的专访稿——《孙儒泳:“生态学是我的生命”》。
以下为原文——

(《中国科学报》 2012-09-24第六版截图)
九月刚开学,记者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届“生命科学青年学者奖”的颁奖仪式上见到了孙儒泳,会场中那唯一满头银发的老者。
已85岁高龄的孙儒泳是这一奖项基金的捐赠人。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为我国生态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他说自己只是想尽些绵薄之力。生态学,是这位老者一生的事业和牵挂。
放弃音乐梦
回忆童年韶光,孙儒泳念念不忘那些在田野和水边玩耍的日子。逮蟋蟀、捉虫子、钓鱼虾……大自然是他幼时最好的玩伴。
多年后,孙儒泳在报考大学时选择了生物系。他自己也不太确定,这与幼时亲密接触大自然是否有联系,因为他的第一个梦想其实是学音乐。
1927年出生的孙儒泳,其求学之路因时势动荡而充满艰辛,抗日战争期间甚至两度失学。1942年,他考入宁波沦陷期间新办的高中师范学校,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音乐教师李平之。
“李老师是宁波市音乐教育界的老前辈,堪称业精为师、德高为范的楷模。”出于朴素的敬仰之情,孙儒泳渐渐爱上了音乐,也弹得一手好琴。
李平之的为人师表,加之音乐的洗礼熏陶,孙儒泳的精神世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音乐,让师生二人成为“忘年交”,并缔结深厚友情。
高中师范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决心要为祖国挥洒汗水大干一场的孙儒泳,却迎来一个晴天霹雳。东迁“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宣称沦陷区颁发的文凭是“假学历”,毕业生是“伪毕业生”,政府不予承认。孙儒泳只好在家待业,备受精神煎熬。
直到半年后,孙儒泳才受邀前往宁波四明孤儿院小学任教,教授国文和唱歌课。
不久,他在与李平之的通信中表达了想上大学继续深造的心愿。在李平之的帮助下,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唐山路小学,白天完成满满当当的教学任务,晚上去夜校补习高中课程。
1947年夏,孙儒泳觉得自己可以冲一把了,考虑投考大学。“音乐学院是我当时的梦想。”然而现实却告诉他,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因为“学费天价,碰都不敢碰”。
再三比较,孙儒泳发现其他名牌大学学费也不低,家庭供养不起。“唯一可供选择的就是免费的师范大学。”孙儒泳把目标锁定在北平师范大学。考虑到自己的意愿和教育基础,他最终报了生物系。
“对于生物,自己多少有点兴趣,相对来讲,也是当时的冷门。”孙儒泳知道,这样的报考选择会有更大的“命中”把握。几个月后,他如愿走进了北师大校园。
人生的关键一步
“老师上课有的用英语,有的用汉语,下课夹着皮包就走了,想见也见不着。”刚走进大学,老师同学之间缺乏交流,孙儒泳觉得自己有点找不着北。
第一次上动物学实验课的“惨痛经历”,孙儒泳记忆犹新。那天的课堂内容是在显微镜下观察草履虫,然后按规定绘出草履虫的外观和所见内部结构。从未摆弄过显微镜的孙儒泳犯了难,又不好意思求助,便自作主张胡乱画了一张交差。
第二天,助教老师拿着孙儒泳的“作品”,上面一个大大的红叉,严厉质问道:“你画的是草履虫吗?”同学们哄笑起来,孙儒泳顿时脸红,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跟上。
一段时间后,孙儒泳从一个入学时连草履虫观察图都画不好的低起点学生,一跃为班上的尖子生。他说这要感谢名师的循循善诱和鼓励提携。
大学期间,对孙儒泳影响至深的一位名师,便是留美归国的著名动物生理学家汪堃仁。“动物生理学是一门讲生理机制的学科,理论性强,比较高深。但是汪先生层层解惑,像说书艺人丢‘包袱’似的讲解,深入浅出。”孙儒泳茅塞顿开,并且在恩师的潜移默化中,立志要专攻动物学。
“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但关键的没几步,北师大的求学生涯对我来说就是个关键。”毕业时,孙儒泳被推荐留校担任助教,他对母校充满感激,“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屁股坐得住,干事情认真不偷懒。这样说,我想自己留校也是够格的”。
担任助教期间,孙儒泳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待在生物系小楼里。准备实验材料、示范标本、解剖用具、仪器设备……集体宿舍中无法安心工作、看书,他每天就在备课室熬到深夜。
捕田鼠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工作出色,1953年学校推荐孙儒泳留学苏联,随后他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突击学习一年俄语。“记得出发时,同行者有一千多人,但只有近一百人是去读研究生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孙儒泳回忆,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整整跑了七昼夜才抵达莫斯科。
来到苏联,孙儒泳选择动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他进入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师从苏联著名生态学家、鼠疫自然疫源地研究权威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纳乌莫夫攻读副博士学位。小导师舍洛夫专攻鼠类生态学,具体指导孙儒泳的生态生理学实验。
经过与导师的反复讨论,孙儒泳确定了论文题目《莫斯科省两种田鼠种群(或叫个体群)某些生态——生理特征的地理变异》,旨在证明地理上相隔不远的两个种群之间,在生理生态特征上可能出现的地理变异。
因论文实验需要,孙儒泳每个季节都要到野外工作一个月,工作内容是捕捉田鼠同时调查田鼠数量,然后回校进行一个多月的实验。实验完成,再去野外,来回往返。
“我留给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师生的印象,大概是整天背着鼠笼鼠夹去野外捕田鼠的,话语不多的,高个子中国留学生。”孙儒泳几乎与老鼠为伴,生怕困入笼中的田鼠晒死、饿昏、冻毙了。
喂老鼠、清洗鼠笼这样的事情孙儒泳都要亲力亲为,他知道,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出差错可能会影响整个实验的精确性。小心翼翼做了两年,孙儒泳积累下上万个宝贵数据。
谈起留苏的最大收获,孙儒泳说,除了科研方法,在学术上善于倾听反面意见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
有一次,针对孙儒泳实验报告中提出的结论,教研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观点大相径庭。“迥异的观点表面看起来令实验者有点尴尬,实际上却大大拓展了我的思路。”孙儒泳认为,人家提出反对意见之处,往往正是自己的薄弱环节,正是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根据各种意见,孙儒泳得到了启发,改进实验方法以加强实验结果的可信度,使原来不同意见双方达成统一。“从反面意见中产生新概念、新思想,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
论文答辩时,孙儒泳接受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四十余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考核,最终以全票评为优秀论文。这是孙儒泳第一次写科学论文,而且是用俄语写作。
完成学业,孙儒泳归心似箭,待学位证刚一发放,他便即刻整装踏上归国之路。
当时,中国兽类学老前辈寿振黄发出邀请,希望孙儒泳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但是我很犹豫。北师大培养我,器重我,送我出国深造,于我是有恩的。”孙儒泳觉得应当知恩图报,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北师大生物系。
逆境中拼搏
回国后,孙儒泳整天都在考虑,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做点具体的事情报效祖国。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国家急需立竿见影的工作,而继续搞哺乳动物生态生理学理论研究,似乎有些过于“阳春白雪”。
孙儒泳主动找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自荐要从事流行病的自然疫源地研究,双方一拍即合。之后,他带领北师大一名助教和两位四年级本科生,参加了该所组织的“柴河林区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野外调查工作。孙儒泳担任鼠类调查组组长,干起了“老本行”。
1959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调查队驻扎在黑龙江的一个林区。队员们以杂粮为主食,不要说荤腥,连青菜都少见。就这样艰苦调查了半年,孙儒泳完成三篇论文,均刊发在《动物学报》上,同年,他被聘为该报的青年编委。
按计划,此次调查活动要延续至冬天,然而入秋后不久,科考队员就被急召回北京,要求必须参加“反右倾”运动。
正是在此次运动中,孙儒泳因缺乏对当时国内政治环境的了解和判断,表达了自己对“庐山会议”的真实想法,结果“捅了马蜂窝”。他被划为“另类”,成为党内大小会议批判的活靶子,被定为“严重右倾”后,业务工作权利随之被剥夺,下放劳动在所难免。
“生物学家应该是最懂得适应环境的,这是达尔文归纳出来‘适者生存’的真理。”孙儒泳回忆,面对逆境,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政治上保持沉默,集中精力在教学和科研上拼搏。
在他看来,科学工作者作出切实的业务成绩,才算真正报答了祖国。
下放劳动几个月后,由于孙儒泳和其他几位同事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被学校召回住院。
1961年,在学校安排下,孙儒泳正式登上大学讲台,讲授综合动物学教改试验课。几个月后,他发挥专长,改教动物生态学。“这是一门解放后全国未曾开设过的新课程。”孙儒泳回忆,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充满风险,因为根本没有现成教材,一切得自己从头做起。
在孙儒泳看来,尽管生态学原理全球相通,但各国动物区系不同,环境也大有差异,因此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中国生态学教科书,必须联系中国实际。他决定,一边讲课,一边编写试用讲义,一届一届不断修订,再最终定稿。
孙儒泳没有想到的是,编写出版这本理想教材的愿望,用了足足20年才得以实现。
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开始后,他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再次被迫中止。“文革”期间,孙儒泳整天闷得发慌,一度在缝纫机上打发时间,为儿女缝制棉衣、夹克……
“那个时候,老鼠还是要研究的,比如灭鼠除四害、防止鼠疫等。”孙儒泳再次主动联系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恳求参加灭鼠拔源工作。得到准许后,他随队远赴边疆地区参加灭鼠拔源和疫源地调查工作。生活异常艰苦,内心却很充实,孙儒泳常年离家,一干就是四年。
灭了四年老鼠,孙儒泳却开始怀疑灭鼠拔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搞这项工作不值得。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判断,采用正面进攻、人工灭杀的方法,往往会使种群繁殖更多、恢复更快。
“科学的个性是老老实实,有一说一。”作为生态学家,孙儒泳觉得自己肩上有推脱不了的责任。
“一只南飞的老雁”
1978年,中国科学迎来春天。“文革”刚结束,孙儒泳受邀参加全国生物学教材会议,会上制定了《动物生态学》教材大纲,他负责编写种群生态学、生态系统、应用生态学和附录四个部分。
改革开放后,孙儒泳先后赴澳大利亚、比利时、美国、英国等国家交流访问,看到了我国生态学的差距,也提升了学术水平。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孙儒泳的研究重心也从野外生态重新回到生理生态理论研究。“做研究工作,创新点还是在理论中,实际应用也必须有理论做基础。”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教师,教学和科研都要有所成就,“千万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从孙儒泳开创动物生态学课程算起,足足20多年后的1987年,他心中那本理想的教材终于问世了,90多万字的巨著《动物生态学原理》凝结着他20多年的心血和汗水。这本专著引发了国内外轰动,被台湾专家评选为推荐公众阅读的十本大陆图书之一,孙儒泳也随之名声大震。
1993年,孙儒泳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那年他66岁。“当选院士,最令我欣慰的是,可以继续为我所热爱的生态学工作了。”他曾在自述中写道,“我无法想象,如果真的从工作中退了下来将会如何。生态学是我的生命,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
此后,孙儒泳继续指导研究生,在动物生理生态、动物种群生态、动物行为生态等领域培养人才,探索钻研。
生态学在20世纪末发展极为迅速,许多分支学科纷纷产生。孙儒泳不断吸收新知识,继续“动手术”修订《动物生态学原理》教材,于2001年发行第三版。
2002年起,75岁的孙儒泳把工作重心迁至华南师范大学,与两个学生一起进行海洋水产研究,每年夏天回到北师大工作。“一只南飞的老雁”,他这样比喻自己近十年来的生活。
“搞了几十年的生态学,我总觉得自己离不开它了。”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孙儒泳在80岁之后不再带研究生,科研活动也少了很多。
采访中孙儒泳告诉记者,他有时候会梦到,自己还像年轻时那样弹钢琴,沉浸在旋律中。从年少时的音乐梦到生物学家,孙儒泳说自己“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优势只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编辑: 陈奉凤纠错:1719646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