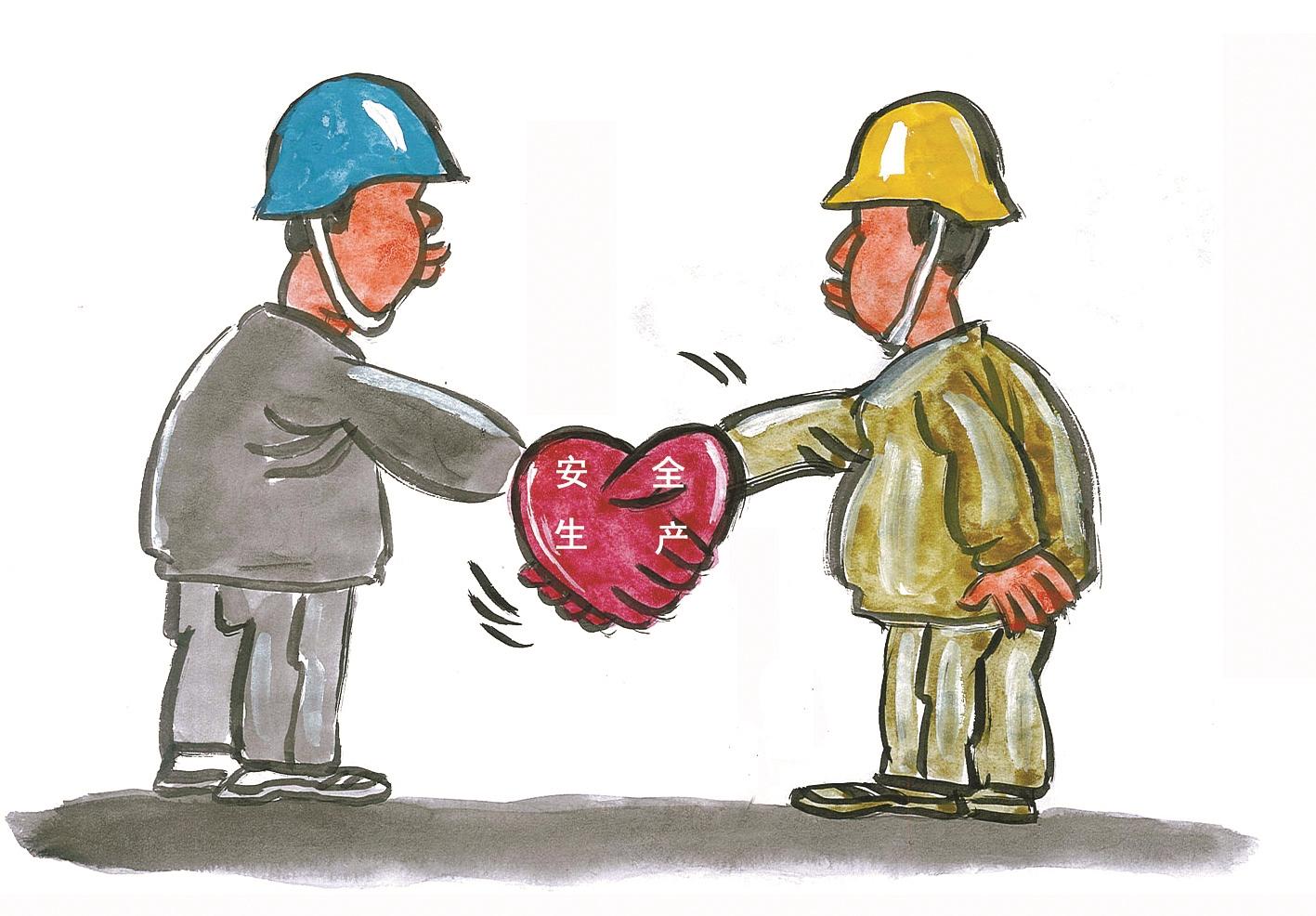六年前的那个夏天,绵阳的空气特别闷热。罗潇和父亲罗平最后一次的交流是在电话里,父亲对她说,自己打算回家做工,工地就在罗潇租的房子对面,离家打工10年后,终于可以回家了。
对于罗平来说,回家是件难得的事。2008年汶川地震,罗家刚好在重灾区边缘,震后重建花光了存款和补贴,还欠了些外债。此后十年里,他一直在青海、云南两地做建筑工人,为了省钱,即便是要坐好几天才能回家的慢速火车,也只有过年才舍得。
如今一家人终于有机会重新一起生活,电话里虽然见不着面,但两人都很高兴。罗潇记得:“我爸说,之后如果干完活太晚太累不想回去,我就住在你那儿吧,等我落实下来,过几天就搬过去,我说没问题。”
然而新的生活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回来工作的第三天傍晚,忙了一天的罗平正收拾工具准备下班,突然晕倒在地。工友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急救,接诊后测体温达41摄氏度。当罗潇接到电话赶去时,父亲已在ICU里陷入深度昏迷,身上放了20多瓶冰冻矿泉水物理降温。
医生告诉罗潇,初步诊断结果为热射病,即重症中暑。她的第一反应是“应该不会要命”,还安慰情绪崩溃的母亲:“没事儿,人已经在医院了,让医生治疗就好了”。
没有想到,经6天抢救,做了两次手术,为了帮助散热,医生还取下了罗平的一小块头骨,但他最终还是去世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里这样描述:“符合热射病并脑挫裂伤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罗潇说不了这么多专业术语,她只知道,父亲死于无法调节的身体高温。

2024年6月12日,西安灞桥区一建筑工地内,当时的地表温度52.9℃。
高温是最致命的极端天气。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加剧,截至2023年,地球平均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了1.2摄氏度。截至今年6月,全球平均气温已连续12个月比工业化前高出1.5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的高温纪录。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可感知的高温天数和热度都在增加,然而人们对于高温的危害认识却始终像是“温水煮青蛙”般不温不火。在一个个看似孤立的悲剧背后,高温致死问题的严重性被大大低估。而要破解这一切,首先要从一个关键的问题开始:究竟有多少人被高温杀死?
被忽视的高温杀手
罗平1967年生,事发时刚过50岁,平时没什么不良嗜好,身体也不错。他没有中过暑,没有高血压等慢性病,除了2012年得过一次胃溃疡外没有其他疾病史;他很少喝酒抽烟,偶尔工作累了,也仅小酌一杯。
出事前几天,他还没有搬到女儿的出租屋里,每天晚上都回家。前一天妻子见到他时一切如常,“看上去挺精神的”;每天一起上下班的工友也没发觉异样,这让事故的到来显得猝不及防。
事发当天,当地的最高气温是32.9摄氏度,待在有荫蔽的地方并非难以忍受;但罗平当天恰好在3米多深的基坑中,四周用混凝土板支护,太阳光无遮挡地直射下来,手边的木制模型都开始发烫。此时,空气不流通加上热量积聚,坑中的体感温度比外头高出不少。
当环境温度超过30摄氏度,尤其是在高湿度条件下,人体的散热功能会开始弱化;当热指数(综合温度和湿度)达到或超过37.8摄氏度时,户外工作或运动的健康风险显著增加。而多数户外工作者很难像一般的高温避险建议里说的那样,“待在室内,保持通风,减少体力消耗”——工作环境与生计需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太多选择。
事实是,同样面对高温天气,不同群体的处境是不相同甚至不平等的。印度可持续未来合作组织研究员巴尔加夫·克里希娜(Bhargav Krishna)告诉澎湃新闻,除了职业之外,年龄、既有健康状况、是否怀孕、住房条件等都决定着个体面对高温时的脆弱性。“老年人、孕妇面临的风险更大;非正规住宅通常没有足够的应对机制,无论是通风、降温设备,还是供水和医疗条件。”她说。
与罗平相似的悲剧每一年都在发生。2022年7月14日,在浙江余姚最热的时候,装卸工人张公前在12平米、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去世,前几天他便出现了中暑症状,“热得难受”,但因请假要扣工资,便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又加了两天班。
2023年7月2日,48岁的导游龚贺带着研学团的孩子们逛完颐和园后,在前往下一站的大巴上昏迷,送院抢救时他的体温升到42摄氏度,距离他出现不适已经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医生判断“送来晚了”,他最终死于热射病。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黄存瑞研究发现,中国的热浪相关死亡人数具有快速增长、非线性和极端性的时间演变特征。过去40年间,热浪归因死亡负担增加了四倍,从1980年代的3679人上升到2010年代的15500人。另外,2010年代的归因死亡人数增速相较于1980-2009年又加快了2.8倍。近年来,其极端性愈加显著,2013、2017、2019年归因死亡人数均超过2万人。
不仅在中国,全球各地因为高温死亡的悲剧也在不断发生。据《卫报》报道,截至2024年7月,美国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法医报告的高温死亡人数为175人,比去年同期增加84%。
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2024年有记录以来最长的极端高温给当地的公共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据印度卫生部数据,印度各地长达数月的热浪已造成100多人死亡;
尽管高温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然而大多数人仍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温导致死亡的人数被远远低估了。据世卫组织估计,2000-2019年间,全球每年有49万人死于高温。但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许多高温死亡并没有被计入官方数字,实际数字可能远远不止于此。
为什么高温死亡难统计?
罗平因高温引发的热射病去世。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个小概率事件,但事实是,高温的威胁始终存在,只不过时常被忽视。
《全球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2023》(下称《全球报告》)显示,2018-2022年,全球人类平均每年经历86天对健康造成威胁的高温天气,其中有60%的发生概率因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而提高。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数据,美国平均每年因高温死亡的人数在702例左右,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高温事件增多,这一数字有上升趋势。2023年,美国有2300多例死亡证明中提到了高温的影响,但佐治亚理工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教授布莱恩·斯通(Brian Stone)认为,这一结果仍然是被低估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指标的分类变化。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计算,1999-2014年,高温作为“根本原因”而导致死亡的人数每年仅有约600人,如果考虑高温作为“促成因素”,死亡人数则显著提升,在某些年份甚至翻了一番。
斯通告诉澎湃新闻:“考虑到所有因素的统计数据,美国每年与高温有关的死亡病例实际接近12000例。”
在两类数据的巨大差距之间,是死亡记录的分类标准不统一、死亡证明的填写和审核不可控以及数据收集和报告系统不完善等重要因素带来的障碍。不同国家、地区、统计主体对高温死亡的分类标准不同,有关指标可能也会随时间修正和调整。许多国家至今仍没有“高温致死”这一统计类别。
罗平去世后,罗潇在律师的建议下给遗体做了司法鉴定,确认其符合热射病死亡。但在其他很多情况中,高温仅作为一种外部因素隐于直接病因背后。
高温死亡归因的复杂性与治疗、登记、认证等一系列死亡信息收集步骤相关,斯通告诉澎湃新闻:“许多与高温有关的疾病患者不会去医院就诊,而与高温有关的死亡要求尸体到达医院后核心体温达到40摄氏度——如果温度在运输过程中下降,则会记录另一种死亡原因。”
在现实中,医生和验尸官在填写死亡证明时,未必能充分考虑高温的间接影响,许多官方的高温死亡记录几乎只考虑中暑这种显然的疾病表现。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大多数与高温有关的死亡并不是由于中暑。高温带来的更大危害是对心脏造成压力,尤其是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因为身体的冷却机制在用力过猛时会对心血管造成压力。这就像腿脚有问题的人却还要奔跑赶公交车一样,肯定会出问题。
华盛顿大学全球健康教授克里斯蒂·埃比(Kristie Ebi)以新冠为类比来描述高温无法被完全记录的情况:由于检测手段的有限性,许多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病例只能被归因于高血压或糖尿病等并发症;同理,如果死亡与高温有关,医生需明确记录,然而,许多高温引发的疾病(如心脏病)可能被记录为主要原因,而非高温。
1995年,热浪侵袭美国芝加哥,气温连续多日超过38摄氏度。那个夏天,官方记录中只有465例热相关死亡,但当研究人员将当时的实际死亡人数与历史同期的平均死亡人数相比较时,发现约有700例超额死亡,多出来的部分很多都被归因于呼吸衰竭或心脏骤停。
“我们在计算高温死亡时只会考虑中暑和热相关疾病,这可能忽略了因高温加剧原有健康状况而导致的其他死亡。”克里希娜认为,“核心问题在于死亡登记的完整性(农村地区的登记率可能特别低)和归因指导标准的严格性。”此外,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根本没有数字化的死亡记录可供查询。
如何提高高温致死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在不同情境中,超额死亡率逐渐成为一些研究者的优先选项,它的要点是将特定时期的实际死亡人数与历史同期的预期死亡人数相对比,把高温放进公共卫生系统和社会历史的纵向发展中去把握。
“这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对死亡的影响。”克里希娜评价道,尽管它也有局限性,“超额死亡人数通常仅在热浪发生几周后才能核实,因为死亡登记与死亡发生的时间通常是错开的,比如在印度是21天。此时,这些数据就无法协助政府提供即时的应对措施,只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如何为下一次热浪做准备。”
无论如何,对高温死亡的统计不断尝试和优化,意味着将气候变局纳入全球健康语境的努力,不再忽视极端高温对健康的巨大影响。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萨里·科瓦茨(Sari Kovats)对此表示:“没有完美和绝对的方法来衡量与高温相关的死亡,其结果取决于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
如何减少高温死亡
父亲过世前,罗潇并不了解父亲在工地上的工作状态,父亲也从来没有同她提过工作的困难或辛苦。在电话中,他往往只简要地讲讲当天做的事,分享些当地的风土人情。罗潇有时会在电话里叮嘱父亲“注意一点喔,天气这么热”或者“去高的地方要小心”,但这些“都只是口头上的”,她对施工环境和设施并不了解。
父亲去世后,她开始经常看新闻,每年夏天都会关注与中暑有关的消息。她逐渐意识到,基本的高温应对和保障措施对普通人而言不可或缺。
“工作时长上得有控制,天气很热的时候真的不建议开工,工地上做事的人大多数年纪偏大了。”罗潇列数着,“工地老板也应该多准备一些解暑的东西,在空旷地带工作的时候,遮阳的场所特别重要。”
2012年,国家卫健委就发布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要求用人单位根据气象预报调整作业时间,配备防暑降温饮料和药品,以及发放岗位津贴;劳动者因高温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但规则从纸面走入现实的过程仍难免曲折——譬如,囿于用人单位的不配合、未在48小时内死亡、能进行职业性中暑诊断资质的机构数量有限等客观条件,罗潇为父亲的职业病认定奔走了近6年,直到最高检察院介入,事件才最终获得转机。但改进终究在缓慢发生,罗平的不幸悲剧激活了四川首例“职业性中暑(热射病)”认定工伤的法律适用规则。
据《极昼工作室》报道,根据近年公开数据,我国一些地区每年报告的高温中暑病例达几百人,仅有个位数申请职业病诊断。有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有出现重症,无法工作、需要入院治疗,甚至死亡时,工人才会想到工伤认定。
长期关注高温下户外工作者生存状况的社会学者于坤告诉澎湃新闻,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户外工作者的绝大部分一直处在被忽视的状态里。
“虽然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健康保障,但在应对夏季极端高温对健康的影响这块其实是不足的。比如说制定了劳动保护法规,那往往是劳动者在健康受到极大损害的情况下才会去起诉所在单位,而且取证过程也很难。”于坤说。
另外,相关部门要求用工单位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健康检查等措施来保障劳动者的健康和权益。但是在实际执行情况中,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此外,公众对高温的认知度也不够。“包括我了解的户外工作者本人,也不觉得越来越热的夏季对健康有极大潜在伤害风险。另外在我看来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心理问题,极端高温天气下会更容易烦躁、焦虑、紧张和易疲劳,更容易发生健康问题。”于坤说。
要减少高温死亡,不仅要关注劳动者权益保护,基础设施和城市规划、医疗和健康监测等方面同样重要。城市中的绿地和水域,能够有效降低城市热岛效应;高温健康风险的早期预警系统,是高温兵临城下时的“第一道防线”。
中国版《2023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指出,2012-2022这十年间的城市绿地变化在我国总计避免了将近3.8万人的过早死亡,28个省份的气象部门在2022年向卫生部门共享了气候数据,2022年热浪和寒潮预警信号覆盖人数达到3185万。
全球范围内,不少国家也开始整合气象行动与健康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也在各方面加强制定和部署警报的能力,包括更新关于热健康警告系统的指南、开发极端高温的标准化术语和定义等等。此前就有专家指出应该像给台风命名一样对高温热浪进行命名。
在应对高温风险的各种努力中,对死亡人数的追踪和统计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其结果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共识与行动方针。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城市实验室负责人阿维卡尔·索姆万什(Avikal Somvanshi)明确表示:“你需要知道这些数字,这样你才能相应地设计你的基础设施和政策。否则,人们会想,哦,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去年只有300人死于中暑。但这不是真的。”
从长远来看,应对高温的行动必然要求综合性的措施。克里希娜认为:“随着我们进入热浪越来越频繁和强烈的时代,建立有效措施来监测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和死亡至关重要。这需要启动全系统的响应,而不仅仅是关注卫生部门。”
对于所谓的“全系统的响应”,柳叶刀《全球报告》中说得更加具体,它包括增强全球和地方层面的健康与气候变化研究和知识生成,完善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监测系统,以及将健康放在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核心位置等。
父亲去世6年后,罗潇才拿到人社局的工伤认定书,有了终于结束的感觉。她找了一个地方,小小地哭了一场。而对于更多人来说,这本是可以预防的。“希望更多人重视高温的危害。不要让我父亲的悲剧在更多人身上重演。”
(应采访对象要求,罗平和罗潇为化名)
编辑: 陈捷纠错:1719646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