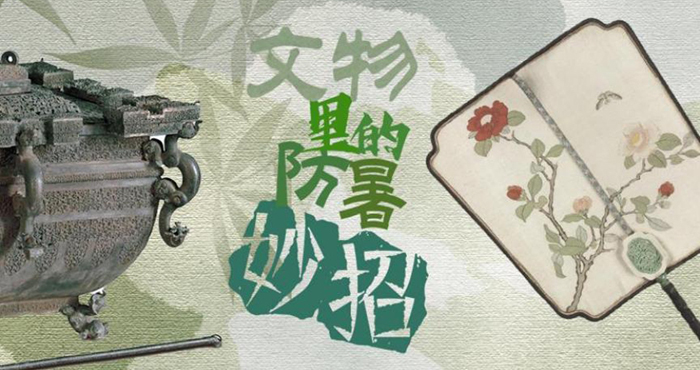“吉金万里”展展出的文物。(本文图片均由唐严 摄)
瞪着大眼睛、挂着肥耳、顶着高鼻子的三星堆人7月22日起在宁波博物馆与观众见面,引起了广泛关注。拥有引以为傲的河姆渡文化的宁波人如何看这个“外星人”?三星堆人和河姆渡人在一起聊天,会不会把天聊死?相差几千年,他们之间存在的不是代沟,而是“鸿沟”。不过,冲着两大文明的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掰扯掰扯异同,或许也会有点收获。

观众在看展。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我们先来找他们的相同点。
毋庸置疑,三星堆和河姆渡,都是中华文明皇冠上的璀璨明珠。虽然两地相隔几千里,但同属长江流域的文明,一个位于长江上游地区,一个位于长江下游地区。他们共同的“母亲”,就是浩荡万里的长江。长江的乳汁滋润着两大文明茁壮成长。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外,从全球视野看,这两大文明都处于北纬30度。这是一个神奇的地带,除了三星堆、河姆渡等遗址,赫赫有名的还有跨湖桥遗址、良渚遗址。即使是被认为不太适合古代人类生存的青藏高原,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存的证据。
如果转动地球仪,顺着北纬30度继续往西,我们还会发现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及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等世界级的文明遗存。
从“江湖地位”来看,这两大遗址都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是人类文明进化中的重要一环,对当代社会均有巨大的影响力。
河姆渡遗址自上个世纪70年代被发现后,颠覆了传统史学“黄河流域中心论”的认知框架,有力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历史地位。
三星堆遗址,是蜀人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长达2000年的物质发展过程的见证,打破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单一认知,也证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展出的铜鱼头杖头铜饰。
文明气魄,风格迥异
谈了相同点,再聊聊不同点。
首先是所处时代不同,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延续了2000多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延续到了晚期。三星堆文明距今4500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西周早期,也延续了2000多年。也就是说,河姆渡比三星堆要早2000多年。
截至目前的考古发现,当河姆渡人在姚江畔用粗糙的石锛和简单的骨耜刀耕火种的时候,三星堆人在地球的版图中还没有留下痕迹。
虽然同在北纬30度,同饮长江水,却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明气魄,这源自孕育他们的土地。
宁波地处宁绍平原,水网密布,气候温润,四季分明,适宜稻谷生长。河姆渡人枕山靠海而居,既有山的坚毅,又有海的广博,形成了海纳百川的开放文明。
而三星堆文明孕育于四川盆地,虽有沃野千里,但山川险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而相对比较封闭。

“吉金万里”展览现场。
一个俯首躬耕,一个昂首问天
接下来,从出土器物来作比较。
来到宁波博物馆“吉金万里”展厅,两件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最先进入观众视野。它们出土于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也是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发现之一。高26厘米、长37.5厘米、宽27厘米的青铜中型面具让人惊艳。
三星堆的文物,就今天的审美来说,其造型设计也不过时。其出土的金面罩、金杖、玉器所体现的工艺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因此不论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最新发现,还是出土文物展,都会引起轰动。
反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有点“灰头土脸”。但因为文明进化阶段不同,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吉金万里”展厅的二楼是宁波博物馆常设展厅,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木器、陶片沾满了泥土的气息。如果去余姚河姆渡遗址公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片木构建筑,那是迄今已知最早的“干栏式”木构建筑。这种建筑式样,是巢居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干栏式”建筑,其木构件中已有成熟的榫卯结构,它反映了河姆渡人的木结构技术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发展历史。
如果要比较的话,三星堆的器物好像是天外之物,它们所寄寓的,是人们对未知领域的想象与迷醉。
而河姆渡出土的粗粝的陶罐,浑圆朴实,当年里面盛放的是散发着清香、金灿灿的稻米,反映的是河姆渡人的烟火日常。
一个是俯首躬耕,一个却昂首问天,两者之间相隔的岂止千山万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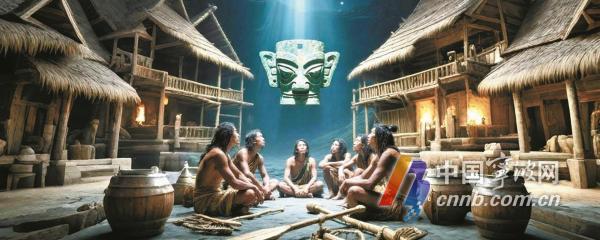
“三星堆”对话“河姆渡”(AI制图)。
知所从来,方明所向
更引人思索的,是二者迥异的命运轨迹。
知所从来,方明所向。李白当年曾感慨“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古蜀国的开创者蚕虫来自哪里?直至今天,都没人能回答。另外一个千古之谜是,辉煌的三星堆文明却在商周之际神秘中断,如一场惊天动地的壮美烟火,骤然绽放于历史长夜,却是昙花一现。
河姆渡则如一条安静流淌的河,其源头是近年来被发现的井头山遗址,而其接续者和拓展者则是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最终汇入中华农耕文明的长河。
这场“三星堆”与“河姆渡”的对话告诉我们,璀璨的烟花固然美丽,令人神往,但拙朴的陶罐盛放的稻谷却是我们真实的依靠,只有朴素而坚韧的耕耘、有节制的使用,文明长河才会生生不息地流淌。
甬派客户端宁波日报记者崔小明
编辑: 杨丹纠错:171964650@qq.com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