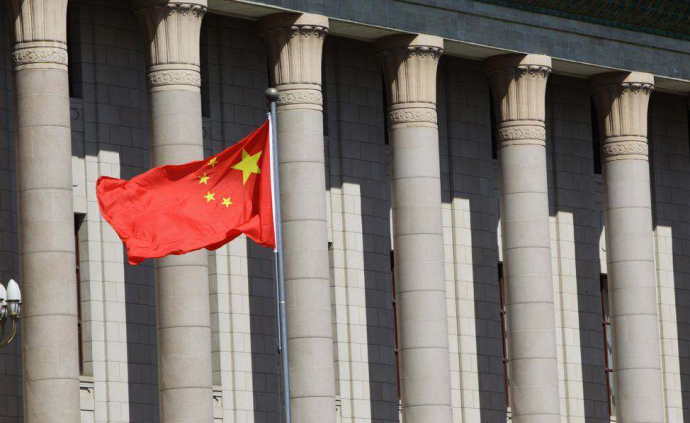5月,“五四”运动的风云正席卷全国,北京的报刊掀起了一场关于五四示威游行事件涉及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的辩论。
争论的各方都没有对游行示威本身提出异义。他们都受过现代教育或现代思想的薰陶,深知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是拥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他们完全有权通过口头、书面和其他手段(集会、游行等等)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五四”集会游行示威,合情、合理、合法。
问题出在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打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梁漱溟提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 学生去遵判服罪。”(9)问题提行非常尖锐,归纳起来是:
1.是不是性质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
2.如何处理“国民公意”与个人自由的关系?
3.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建立真正的“民国”?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藉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乃至今日都会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不过,这貌似荒唐的主张体现着一个思想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
反对梁漱溟主张的意见占上风。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点:
一是法律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他们说:“我们人类现在既已承认学生运动是合乎正义的,国家和法律也应该跟着我们人类往一条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认,法律上不承认的话,是野蛮时代的法律,专以维持秩序作目的的……这种法律观,单是救济人治之弊的,在现在的国家内,实在没有什么功用。”(10)
二是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 ,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给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11)
保障公民自由,让中国人摆脱奴隶心态和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始终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青年》杂志从创刊之日起,便严正宣告:“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12)“须有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之雅量,不得恃多数之威势 ,抹煞异己者之主张。"这是不应违反的"金科玉律”!(13)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道德义愤空前高涨 ,群众出现了失控的过火行动,思想家们面临要不要维护新文化运动基本宗旨的严重抉择。
多数人迷惘了!他们认为以“正义”、“国民公意”、“群众行动”的名义,就可以侵犯个人的自由。这个思想迷误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开端。几年后,国民党承袭了这个侵犯个人自由的观点,把它推衍到极端,在“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的旗号下,以“革命”和“国民”的名义,建立了剥夺个人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专制统治。其灾难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接受这一思想影响不是偶然的。其主要领袖孙文在辛亥革命后一再公开宣扬反对人个自由的错误观点,极力在中华革命党内建立个人独裁制;(14)再加上苏俄的消极影响,一个反民主、自由的畸形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从五四爱国运动中得出一些偏颇的认识。他们不是把五四那样的群众运动,看作改革当时名不符实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手段和推动力量,而视之为夺取或摧毁现行制度的手段。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15)要民众用“直接行动”达到自己的目的。本来,偏颇乃至极端的观念所在皆有,在正常的情况下,它可以在自由讨论中逐步化解。但当时的武装力量都归某一武人或党派所有。这些偏颇观念与武装力量相结合,强制推行,以“革命”和“国民”名义建立极权统治就成为现实了。
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态度有所不同。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维护和扩大个人自由。胡适和蒋梦麟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提醒学生,最不可少的精神之一是在团体生活中 ,要“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16)
他们发表这些意见也蕴含着对社会制度的认真思考。在他们看来,首先要敢于拿世界现代文明的成就为参照系,以批判的态度深刻地进行民族自省,勇于揭露本国有那么多“不如人”之处。其次,深信“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17)在原有基础上,切切实实地改革,一步一步前进。再次,深信现代社会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有充分的言论和集会结社等自由。为此,积极组织和参与扩大自由度的抗争。例如,他们和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不受限制的自由,要求废除袁世凯及其继承者制定的五个侵犯公民自由的法令。
当北京发生暴徒火烧《晨报》事件,而陈独秀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的时候,胡适十分沉痛地指出:“《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示必真非。’……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而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8)他们坚持新文化运动的初衷,而同立志要弘扬孔家学说的梁漱溟在争自由这个不容含糊的重大问题上互相呼应了。
不幸言中,几年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就建立起来了,新文化运动也随之被扼杀,没有完成思想革命的历史重任。
历史不可能重演。在饱尝以自由为祭品的“大革命”苦果后的中国人,重温这段尘封多年的争论,也许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历史智慧。
原载《同舟共进》1999年第5期,广州;《南方日报》1999年5月31日。
编辑: 张晓纠错:1719646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