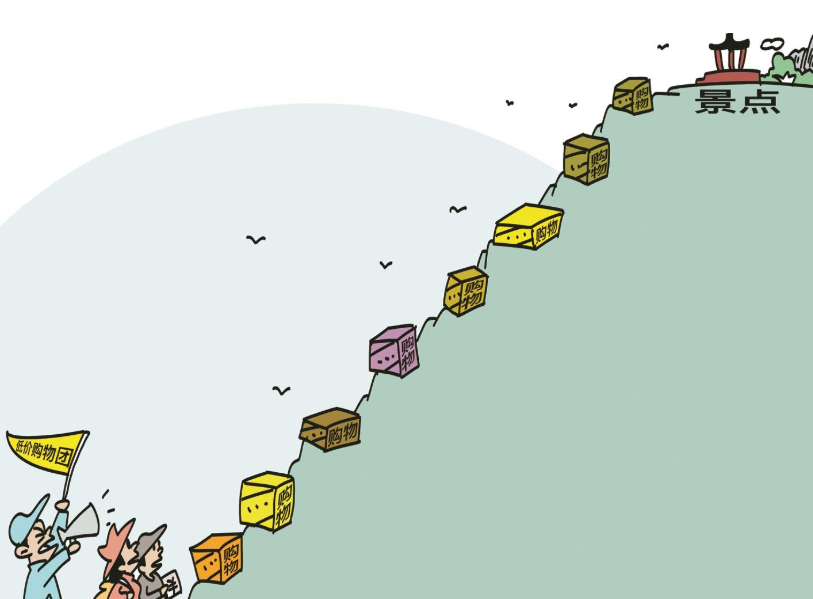“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在宁波考古70年的恢弘长卷中,越窑青瓷无疑是最璀璨的篇章之一。它不仅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成熟青瓷,更在唐宋时期成为全球青瓷生产与贸易中心,以窑址数量、秘色瓷技术、外销规模“三最”成就,书写了中国陶瓷史的传奇。
文明启幕:从“母亲瓷”到上林湖核心
陶瓷史上的“质的飞跃”,并非一蹴而就。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夏商之际,原始瓷就已出现。至公元1世纪的东汉中期,这种“过渡性”器物才完成蜕变。“越窑就像中国陶瓷夜空中最亮的启明星。”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沈岳明如此比喻。
上世纪80年代的科学测试证实,东汉越窑青瓷的抗弯折强度、吸水率等指标,已与现代瓷器高度接近。这一工艺上的突破,让越窑赢得“母亲瓷”的美誉——不仅是最早的成熟青瓷体系,更在千余年烧造史中,深刻影响了高丽瓷、日本陶器等东亚瓷业的发展。
越窑的核心,并非自始至终都在上林湖。早期越窑重心在曹娥江流域,东汉时期上虞有百余处窑址,而上林湖区域仅发现约十处。这种格局的转变,始于中唐,盛于晚唐五代。
上林湖的崛起,源于“天造地设”的自然禀赋与精准的工艺革新。这里优质瓷土储量丰富,丘陵地形适宜建造十几度坡度的龙窑,40米左右的窑长能保证烧造的稳定性;东横河连接浙东古运河,瓷器可顺流直抵明州港,通江达海。而匣钵的普遍使用,为瓷器筑起“防护罩”,隔绝烟火与沙尘,让釉面变得光洁莹润。
沈岳明认为,唐玄宗“禁珠玉锦绣”政策让金银器退出主流,叠加陆羽《茶经》“越州上”的品评,共同推动越窑青瓷成为宫廷与市场的宠儿,越窑青瓷生产规模随之爆发。考古发现印证了当时的盛景:慈溪南部不足4平方公里的上林湖湖区,分布着115处窑址,加上古银锭湖、白洋湖等片区,总数180余处。“单位面积窑址密度之高、保存之完好,在中国窑址中首屈一指。”慈溪市文物保护中心原主任、研究馆员厉祖浩指出,这种密集程度,使其成为唐宋时期越窑无可争议的核心窑场。
巅峰之作:秘色瓷的千年传奇
在越窑家族中,秘色瓷无疑是“顶流明星”。
“1987年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的主持者沈岳明回忆道。当时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14件青瓷,伴随着记录详细的《物账碑》,终于让只存在于文献中的秘色瓷露出了真容。
为解开这些绝世珍品产地的谜团,浙江省2013年启动了“越窑五年计划”,对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展开了精细发掘,发现这里就是晚唐五代秘色瓷的“旗舰工厂”。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发掘,破解了秘色瓷生产技术与贡瓷地位问题,其也入选了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后司岙窑址的发掘堪称“石破天惊”,这里不仅有完整的窑场格局,更出土了大量与法门寺秘色瓷形制、工艺一致的标本,包括八棱瓶碎片;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记载:唐懿宗“恩赐……瓷秘色椀七口……”而后司岙窑址有一件刻有“罗湖师秘色椀”的匣钵,其上“秘色椀”三字,与《物账碑》记载完全一致;独特的瓷质密封匣钵工艺也首次被揭示。
厉祖浩揭开了秘色瓷的烧造秘诀:“胎釉并无特殊配方,核心在‘精做细烧’,装窑时用瓷质匣钵密封,接口以釉封口形成弱还原气流。”这种工艺烧出的瓷器,釉色青绿淡雅,光泽如冰似玉,完美诠释了“千峰翠色”的意境。
考古发现更厘清了秘色瓷的烧造脉络:始于唐大中年间,盛于晚唐五代,延续至北宋初,所谓“秘色瓷”是烧造前就确定的品类,而非事后品评的“精品”。
1998年发掘的寺龙口窑址进一步突破认知——这里的南宋地层,将越窑停烧时间从北宋末推迟至南宋初,寺龙口窑址发掘同样是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丝路通衢:跨越海洋的文化使者
唐宋时期的上林湖,不仅是生产中心,更是全球青瓷贸易的“心脏”。中唐以后,越窑青瓷通过明州港扬帆出海,开启规模空前的外销史。
“8世纪后期开始,越窑青瓷成规模登陆日本列岛,这段贸易往来持续了近三百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副教授山口博之的研究数据显示,在日本出土的中国瓷器中,越窑产品的占比高达81%。
印尼海域的井里汶沉船,是这段贸易史的“活档案”。这艘吴越国晚期的商船,打捞出水了50多万件货物,其中越窑青瓷超过30万件。厉祖浩证实,这些瓷器的胎釉特征、装烧工艺,都能在上林湖窑址找到对应标本。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再到东非肯尼亚拉穆群岛,越窑青瓷的足迹遍布古代世界。
宁波是这场贸易的核心枢纽。和义路码头的唐代青瓷碎片、永丰库遗址的“保税仓库”痕迹,都见证着“港口—仓库—市场”体系的繁荣。
影响更深远的是技术传播:沈岳明发现,韩国窑址中刻有“奉化”字款的器物,暗示宁波窑工可能跨海传艺;山口博之则观察到,日本对越窑青瓷从“代购”到“仿制”,最终实现本土化生产;厉祖浩解释,朝鲜半岛高丽瓷创烧时,龙窑结构、匣钵形制等核心技术几乎全盘移植自越窑。越窑青瓷的出海之路,是从“卖产品”到“传技术”的文明交流之路。
回望越窑的千年历程,从东汉的“第一片成熟青瓷”,到唐宋的“全球青瓷枢纽”,它以窑址数量之密、秘色瓷技之精、外销规模之巨,在中国陶瓷史乃至世界贸易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见证着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厚重历史。
宁波日报 甬派客户端 记者周晓思
编辑: 陈捷纠错:171964650@qq.com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