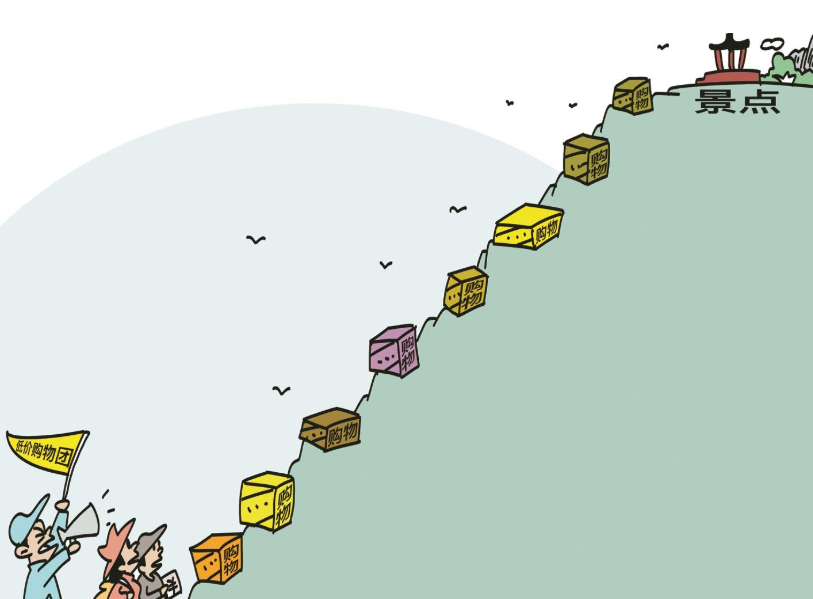大榭遗址坐落在宁波北仑大榭岛涂毛洞山南麓。2016年至2017年,经过系统性考古发掘,这座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遗址重见天日,见证了一场从“靠海吃海”到“煮海用海”的文明跃迁。
在宁波考古走过70年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近这段跨越数千年的海洋开发史诗,叩响东南沿海先民与海共生的智慧之门,探源那道改写中国制盐史的文明曙光。
在“宁波考古七十周年特展”的“煮海”展区,那些斑驳的陶器、古老的灶台与灰白的钙质结核,无声地还原着4000多年前的制盐场景。
“遗址中发现了成组排列的煮盐灶坑和大量制盐废弃物堆积。出土的制盐陶缸、陶盆、支脚等工具,虽形制简陋,却承载着一项划时代的创举。”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大榭遗址考古领队雷少说,这些看似朴素的遗存,见证了大榭先民从刮盐泥制卤到煎卤成盐的全过程,开创了中国海盐生产的先河。
考古研究揭示出其持续优化的生产工艺。盐灶形态从早期单一灶眼,逐步发展为多火眼并列的“高效灶”,最多可达七眼同时作业。配套的制盐陶器同步升级——从厚重的大口陶缸演变为更易于挥发水蒸气的平底陶盆,陶土中还掺入植物碎屑与贝壳粉以提高耐热性能。
这些发现不仅再现了4000多年前的制盐场景,更展现了大榭先民在工具改进和工艺优化上的持续探索,见证了中国海盐生产从起源到发展的技术脉络。
古人云:“天生曰卤,人生曰盐”。盐,不仅是“生命的食粮”,更是推动文明进程的关键物资。
大榭遗址所代表的海盐生产,已超越家庭副业,迈向专业化、规模化。雷少说,渔盐之利,是海洋文明的“接力棒”。盐既能用于腌制海产品,也可通过贸易网络输往内陆,换取粮食等必需品,这种刚性需求让盐业稳稳占据沿海经济的核心地位,成为连接山海、撬动区域贸易的关键支点。
至东周时期,越国因经济社会发展之需,大力推动盐业规模化生产。大榭岛上的制盐业由此跃升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考古发现表明,仅大榭遗址东北侧就分布着至少9处商周时期制盐遗址,印证海盐生产已成为那个时期当地的支柱产业。
盐业所蕴藏的巨大经济利益与赋税潜力,早在春秋时期就已被充分认知。管仲推行“官山海”之策,专营盐铁,使齐国国力强盛而成霸主。越国效仿此道,将盐业纳入国家经营,包括大榭岛在内的东南沿海盐业,在区域整合与国家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大榭遗址的价值远超技术本身。其作坊式生产区与居住区分离的布局,表明这里已形成外向型专业经济。
在浙南山区(今丽水地区)的好川文化聚落中,考古学家发现其人口空前增长却缺乏本地盐源,其食盐需求很可能依赖沿海输入。与此同时,大榭岛及舟山群岛多处遗址发现盐业纯生产作坊,进一步印证跨区域盐业贸易的存在。
一个以盐为纽带的早期贸易网络逐渐清晰:沿海以海盐交换内陆物产,促进资源流通与文化互动,为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注入动力。
“将大榭遗址置于中国盐业考古的宏观视野中,其开创性地位愈发清晰。”雷少说,与依赖地下卤水制盐的三峡地区、山东半岛等地的先秦盐业遗存不同,大榭遗址代表了直接利用海滩盐泥提取卤水煮盐的早期技术体系,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盐手工业遗存。
在年代序列上,大榭遗址所处的钱山漾文化时期,比山东寿光双王城商周时期的制盐遗址早数百年,也早于以尖底杯为特色的三峡地区中坝遗址制盐传统。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指出,大榭遗址所见的盐灶结构与制盐陶器,与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早期盐业遗存高度相似。他说,这类遗存在我国舟山群岛、香港、珠海等地也有发现,但长期被误认为“烧烤炉箅”,大榭遗址的发现首次确证了其制盐功能,堪称“我国沿海地区目前已确认最早的制作海盐的考古实证”。
大榭先民的制盐智慧穿越时空、千年未绝。宋代词人柳永在明州昌国县(今舟山定海)任盐监时所作《煮海歌》中“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咸味加”之句,正是大榭先民“刮滩淋卤法”的生动写照。
这项古老的制盐技艺,历经世代传承,至今仍在宁波象山大徐镇杉木洋村等地延续,被老一辈盐工以古法复原。2008年,象山海盐晒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不仅是浙东地区海盐生产史上的重要记忆,更成为我国古代海盐制作工艺存续至今的“活化石”。
宁波日报 甬派客户端 记者黄银凤 见习记者冯姝涵
编辑: 陈捷纠错:171964650@qq.com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微信公众号